《根本恶》经典读后感有感
|
《根本恶》是一本由[美] 理查德·伯恩斯坦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页数:3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根本恶》精选点评: ●人之初,性本恶。善不是天性。在信仰和社会道德坍塌的世界里解放天性,只能一片黑暗。 ●文献梳理清晰,理解没有大的偏差,不过书的整体性较弱,虽然做了些整合,但显然还是一本拼凑起来的论文集。 ●奥斯维辛之后,恶的存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在这片泥潭中,伯恩斯坦仍然试图向前,而且他的梳理显然卓有成效。 ●谢林和弗洛伊德的部分真好,赞美谢林。ps:上乘的翻译 ●复数的情感在面对过度的恶时往往是贫乏的、失语的。一种智性、深刻、精细的话语也因囿于个体在具体的恶的现实面前夹缠无力。我们为无意义的苦难寻找形而上秩序和伦理的恰切性的倾向乃是非道德的和危险的。 ●非常棒!既是对恶的理论的梳理,同时也可以看作对多位哲学家思想脉络的入门。从根本上说,“根本恶”是“平庸的恶”的前提,而杜绝“根本恶”,起初依靠的是伦理,但当伦理由于人自以为的“强大”而濒于崩塌,或许我们只能诉诸责任——“不作恶”的责任。然而和“人性的,太人性的”内容相比,这种责任意识似乎无力形成约束。但多一份对恶的讨论,或许就会多一点希望。 ●极好,尤其是谢林。 之后再补笔记(懒死) ●康德:严格主义的根本恶:不将道德责任置于第一动因;列维纳斯:恶的过渡性,不可综合性,超验性,反-神义论性质;阿伦特:根本恶将所有人视为多余,成为历史秩序实现的工具。剥夺人的法律属性,道德属性,最后剥夺所有复数性(自发性,不可预测性);本体论帝国主义;康德,尼采,列维纳斯,妥思对无终极意义提出的解决方案:普鲁士式的责任精神,树立新的道德价值,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虚无主义。 ●好好好好好好 ●坚持把尼采看作是辩证法大师,尽管尼采自己很看不起辩证法。 《根本恶》读后感(一):关于恶的(近代)思想史 这是最近看得最仔细的一本书。本书对康德以降的西方重要思想家关于恶的问题的探讨做了详尽的综述和剖析。从中我们能看到一条发展的脉络,同时也能做出有益的比较,发人深思。翻译得很好,注释和参考文献都做得很严谨。将来可以考虑译介基督教传统对恶的分析,那是一个更庞大的思想资源。如Augustine的论摩尼教,Aquinas的De malo,Anselm的三篇哲学对话等。 《根本恶》读后感(二):哲学的穷困 道德哲学之荒蛮并非到今天才这样。时人论道德,简直惨不忍睹。对康德,只能说应该剥夺康德说话和写字的权利,康德滥用语言文字登峰造极,相比费尔巴哈只是本来就思维混乱,这更是不可饶恕。单纯、绝对、根本作为补锅匠简直就是武装到眼睛却暴露了命门。在这个后维特根斯坦时代,在后散文诗的时代,再不济,在这个后阐释学、叙事学、结构主义的时代,还能对滥用语言本身时的有限的人的动机毫不察觉的人才配得上做这样略备一谈的废品的作者。康德太狭隘了。人的一切问题都是时空悖论。而康德将之绝对理念化,拼了吃奶的劲否认时空和悖论,境界只限于矛盾和合理性,害怕一切极限的延伸,害怕得瑟瑟发抖、屎尿横流。理性英雄主义也只是做得了无理性的哲学偶像崇拜的对象。非理性英雄主义者最终却疯了。康德自负时就说纯粹,黑格尔攻击时就说朴素。偷换概念和自欺欺人,凌空蹈虚的程度丝毫不亚于老庄,对,就是化了妆了老庄而已。甚至更不堪。他们否定超验,就生造本体,为了避免尴尬就避谈太远的东西。黑格尔隐晦掉时空悖论即人的有限性,而偷天换日,区区一台电脑想自信替换机器语言的二进制结构,形同梦游。理性哲学中隐藏着太多幻觉和白日梦。文字学会了深刻的欺骗。 《根本恶》读后感(三):齐泽克的黑屋与恶之平庸 齐泽克的黑屋与恶之平庸 齐泽克提到过一篇短篇小说《黑屋》。它讲述了在一个美国小镇,有一间神秘的黑屋。这是村子的禁区,人们不能靠近黑屋,否则将会有性命之忧。传说里面还有鬼魂和疯子。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来到村子,听说了这个故事,便前往黑屋一探究竟,结果发现黑屋仅仅只是一间普通的,破败的屋子罢了。他向人们讲诉了他的发现,结果被惊骇的人们打死。 这个故事不是正好与阿伦特所谓「恶之平庸」相似吗?如书中所说,当思想试图达到某种深度,刨根问底,而当思中所说想开始考虑恶的问题,它便要遇到挫败,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恶的“平庸性”,这便是解释艾希曼身上发生的事情时所遇到的困境。 仔细想一想,奥斯维辛不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禁区」吗?哪怕现代人已经渎神,也不敢否定奥斯维辛的罪恶性。可以说,奥斯维辛是现代的复生的神,奥斯维辛之恶是最大的最不能反驳的人类常识。 如果以此观之,如果某人说出奥斯维辛这个「黑屋」一无所有,那么我们必将严厉谴责他,正如黑屋故事中人们“杀死”工程师一样。 无怪乎当阿伦特指出恶之平庸的时候,会受到那么多的谩骂和指责。 1.承认某种深度的根本恶,却有承认“恶魔般伟大”的危险。2.承认恶之平庸,却有滑入恶之一无所有的危险。 这是两难的困境,仿佛遭遇了海德格尔之存在的情况,我们身处于它却又一无所知。而至于我,或许仍然也是某种齐泽克的立场。 奥斯维辛是人类至今未知最大的创伤,而历史,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符号化却又反复失败的进程。 《根本恶》读后感(四):啊,好恶啊 一、 奥古斯丁曾言,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我本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你问我,我倒觉得茫然了。许多概念我们都是日用而不深究其意,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流与理解。但“恶”这个概念却使我们焦虑不安。以奥斯维辛的浩劫为象征,20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斥恶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体系、道德观念不断翻新、无所定论的时代。于是我们无数次使用“恶”这个概念,试图以此澄清自己对种种历史事件、日常现象的感受,然而什么是“恶”却不再有自明的答案。这个概念不再是一个称手的工具,这逼着我们对它作出概念层面的说明。 但这些现实情势并没有刺激出相应的智识努力。回顾20世纪学术史,除了阿伦特(也许还要算上斯科拉),我们找不到一个为“恶”殚精竭虑的思想家。主导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概念是功利、自由、正义、权利、社群、美德等等,唯独没有“恶”这个在20世纪历史经验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概念。神学中对“恶”的研究则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局限在一套狭隘的话语体系中,专注于探讨“恶”的出现与对上帝的信仰如何调和的问题。事实上,在晚近的哲学讨论中,颇有些人认为“恶”是个缺乏解释力的概念。这些论者认为,在使用“错误”、“没有价值”等“恶”的相近概念时,我们对其所表达的意思都有着较为明确的把握。只有在没法理解某种行为,因而没法用我们自然理解的概念解释它时,我们才会使用“恶”这个概念。但“恶”并没有澄清贴上了这一标签的现象,“恶”只是覆盖我们理解滞涩之处的遮羞布。 在《根本恶》一书的前言中,作者伯恩斯坦自叙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他对哲学就形成了苏格拉底式的理解,即哲学困惑植根于日常经验,哲学探讨则致力于澄清这些经验。20世纪对“恶”的日常体验与哲学把握极度不对称这一思想背景,作者苏格拉底式的治学旨趣,以及他作为阿伦特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事实上,产生此书的直接机缘就发生于作者写作《汉娜·阿伦特与犹太问题》一书的过程之中——几条线索交织到一起,促成了《根本恶》一书的写作。 二、 对恶的考察是一项哲学工作,作者开展这项工作的方式并不是对“恶”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也不是凭空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在其中独断地给出“恶”的定义。此书以“恶”为线索,探究了康德、黑格尔、谢林、尼采、弗洛伊德、列维纳斯、约纳斯、阿伦特八位思想家在此问题上的观点。这当然是一项哲学旨趣的而非单纯历史的研究。作者不是将前人的思考看作既成之物,对之进行“客观”述评,而是把先哲视为对话者,与他们交锋、向他们学习,希冀在这一对话过程中丰富我们对“恶”的理解。 研究方式并不是外在于研究的手段,而是一项研究的构成性因素,选择何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是由作者的实质性观点决定的。伯恩斯坦从根本上怀疑存在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澄清“恶是什么”的理论。对“恶”的探究处在诠释学循环之中,这一思想处境决定了这种探究是永远谈不上完成的。我们必须向种种日常经验和思想资源敞开自己的视域,邀请它们加入关于“恶是什么”的永恒对话。 三、 此书以康德开篇,至阿伦特终章,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恶、意志与自由”讨论了康德、黑格尔和谢林对“恶”的分析;第二部分考察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题为“恶的道德心理学”;在第三部分“奥斯维辛之后”中,作者分析了列维纳斯、约纳斯、阿伦特这三位生平、学术有大面积交织的犹太学者对“奥斯维辛之后”如何思考“恶”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 如果我们追随作者的运思逻辑,在正式进入文本前也许可以简单浏览下阿伦特部分。作者本人写作此书正是受了阿伦特的启发,而阿伦特对康德的引用则使作者产生了考察康德的兴趣。处理康德自然带出了黑格尔和谢林在同一思想脉络中的进一步工作。作者特别强调了谢林的重要性:谢林的工作具有转型意义,即他对“恶”的探讨不再纯粹是古典哲学式的,而开始具有了道德心理学色彩,触及了“恶”之禀性的无意识维度。这又引出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虽然他们与谢林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学术传承关系,而只有些表面上的相似性可堪比附。第三部分之所以分析列维纳斯和约纳斯,自然是因为他们与阿伦特在生平与思想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从而进入了作者的研究视野。可以说,作者从阿伦特出发,通过追溯各种线索,搜集了这八位思想家对“恶”的思考。借助这一搜集工作,作者从阿伦特那里得到的问题获得了更宏阔的思想图景和更丰富的反思可能,“奥斯维辛之后”的问题也变成了一个现代思想的共同问题。 但坦率说,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有些取巧,细究下来并无太多深意可挖。作者选择这八位思想家有各种琐碎的理由,但缺乏明确且一贯的旨趣。作者对每位思想家的介绍都称得上博学多识、文思晓畅,但整本书似乎不存在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一条层层递进的论述线索,既没有梳理出思想史的明确脉络,也没有塑造出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对话结构,看不出他们的交锋点在哪,彼此能相互补充的不同面相又是哪些。 例如,作者之所以处理康德,似乎仅是因为阿伦特在书中提到康德是“根本恶”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但某一概念的第一次使用很可能是出于偶然,因此只是琐碎的历史趣闻,并不一定具有思想上的重要性。从作者对康德的处理来看,他也确实没能在康德与阿伦特之间建立起值得一提的思想联系,没有展现康德在何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道德的思考方式,从而是我们思考“恶”时必须返回的起点。 又比如说,作者认为,黑格尔将“恶”解释为绝对精神运动的一个必要阶段,因此“恶”将被后来的阶段所扬弃。这是一种具有神义论色彩的对“恶”的证成。作者在分析黑格尔的最后一节评论道,在经历奥斯维辛的深渊之后,我们无法再相信黑格尔对“恶”的证成了;但黑格尔拒绝将恶本体化,强调人与恶相遇时的斗争,黑格尔的这一面是值得我们“挪用”的。作者的这些评判显然只是在以一种未与黑格尔深入交锋过的先见外在地阅读和挪用黑格尔,使之不偏离主题太远。如果说从全书来看,处理黑格尔的这一章略有些离题的话,那么在这一章中,为了回到主题而写的这最后一节又有些像离题话了。这真是“否定之否定”了。 无独有偶,在分析尼采时,作者先是凝练地介绍了《论道德的谱系》的基本观点,再以“辩证反讽家”来解释尼采道德批判的真正教诲:肯定意志、克服虚无主义。在完成这一工作后,作者又在此章末尾解释了“恶”与憎恨的关系。如此一来这一章似乎就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尼采道德批判简介了,而挂到了“恶”这一主题之上,并且揭示了“恶”的一个重要面相,即它与憎恨的联系。 概言之,作者似乎只是简单罗列了几位或是公认比较重要、或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思想家对“恶”的思考,使全书各章成为一个整体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恶”这个主题的共同性。全书各章、各节的标题就给人以罗列感:形形色色对“恶”的思考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却找不到一条能将它们串联起来的线索,不明白当伯恩斯坦教授谈论“恶”时,他到底想谈论什么。我们于是只好大而化之地说:他想谈论“恶”。但事实上,本书书名却是“根本恶”,因此书的主题本应限定在“根本恶”上,而非远为宽泛的“恶”。但从作者的实际处理来看,“根本恶”这一问题却并未获得主题地位,而只是和“神义论与恶”等并列的一条次要线索而已。总之,此书尚未触及真正的哲学研究,尚未在这些思想家之间、在作者和这些思想家之间建构起深入的对话,在性质上更接近一系列以“恶”为主题的论文结集。 这些自然是求全之毁。在“恶”这样一个艰深且少有人问津的题目上,我们不应强求作者提供更多。查尔斯·泰勒的评论颇为公道: “……伯恩斯坦带我们领略了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也最具洞见的思想家,以他们的思想引领我们的求索……读完本书,恶的问题仍然令人困惑,但是我们已经有所收获,也获得了继续思考的力量。就这个主题的著作而言,这已经是一项非常卓越的成就。” 《根本恶》读后感(五):《根本恶》(Radical Evil)读书笔记 【导论】 作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当今人们普遍感到神义论与我们不相干,而当我们给某事贴上恶的标签时,我们缺少一种足够深刻、足够丰富、足够精细的话语来捕获已被体验到的东西;康德创造了“根本恶”,黑格尔的体系里恶被证明是人的发展与精神的一个必然阶段,同时还存在对这个恶的必然扬弃,这在“精神的伤口治愈了,没留下任何疤痕。”这句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谢林架设了一座桥梁,为从古典哲学对恶的处理通向道德心理学对恶的处理做好了准备;弗洛伊德和尼采随后分别对恶进行了道德心理学分析;三个犹太人Levinas、Jonas、Arendt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海德格尔的失败——未能有效回应20世纪之恶及人类对这种恶的责任。 【第一部分 恶、意志与自由】 【第一章 根本恶:自相矛盾的康德】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里使用了“根本恶”的表述;他区分了意志(Wille)与意力(Willkür),意力是指在可选项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从本质上说,它既非善亦非恶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自由选择善恶准则的能力”(p14),两者的区别在于:意志是【立法功能】,意力是【执行功能】,Wille是Will的规范性方面,它没有行动的自由,但也没有承受限制或压力,相反,它向意力(Willkür)施加了自己规范性的、理性的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就都是由自由选择能力(意力)的行动者,但是“拥有选择能力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无所偏向的。相反,如果我们响应作为道德规范——作为自由法则——的意志(Wille)的命令,我们就是自主的”(p15)。 【恶的准则】 恶来自于自由意志而非自然: 康德实际上并不认为“我们的自然倾向是人类之恶的根源”,而是强调——“由于人类具有意愿能力,因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采用的善恶准则负有完全的责任”(p16),“一切罪、恶行与德性都起源于(自由的)意力”(p16),自然不会产生恶,只有人的自由意志才会产生恶。 善恶的区分关键并非在于诱因本身,而在于诱因的排序: “对于康德来说,在决定一个准则是善还是恶时,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这个准则是否“包含”遵循道德法则或我们的自然倾向的诱因。相反,问题是这些诱因如何排序——哪一个诱因是第一位的,哪一个诱因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是从属的”(p17),而恶就在于颠倒了诱因的道德次序。 道德价值在于义务: 康德注重动机,富于同情心而做某件事的人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因为他不是为义务而行动;因为此时此人优先考虑的是他的同情心(一种自然的倾向)而不是道德义务的要求,“这一范式,在康德看来是恶的准则”(p20),因为这些起因与法则相一致是纯粹的偶然,它们完全也有可能使得意力违背法则(今天不作恶,明天也有可能作恶,只要没把善当作法则(义务)来遵守,它在经验上就是不穷尽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是恶的,不是因为他所做出的行动是恶的,而是因为这些行动具有这样一种性质——我们可以从这些行动中推断,在他心中存在着恶的准则”(p20),这是一种严格主义的二分法。 【根本恶】 康德事实上对人性的看法是:“我们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p22),这一方面使他怀疑启蒙运动那种道德进步的观念——那种认为借由道德进步人类可以(并将要)取得人的完善,另一方面只要人类能够凭借他们的自由【在实际上】变成善的,那历史上就可能存在道德的进步(此处洛维特对康德有过批评)。 两个世界与一元论: 康德在现象(phenomena)与本体(noumena)之间做出了区分,但二者之间如果没有交互作用,就无法一以贯之地理解他的道德哲学;Korseggard认为两个世界之间是有交互作用的,理解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彻底区分是关键,“康德的自由理论并没有使他陷于本体论的二元论”(p24),“康德有一个【一元化的人类行动者】概念,这个行动者既是自由的,又受到自然因果律的制约”(p24);由此康德区分出德性现象(virtus phaenomenon)与德性本体(virtus noumenon)。 在康德对根本恶的分析中,他并没有被束缚于两个世界的理论,因为他有一个前提——对“人性”的谈论要具有可理解性;“我们作为人类,可能有在道德上成善的禀赋,但只有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力,我们才能在道德上实际地变成善的(或恶的)”(p25),善的禀赋≠善,向善≠实际善;“人实际上的善恶并不取决于人对这些禀赋的拥有······道德上的善恶概念涉及的是人对其能力的【实际运用】”(p26,因而是一种实践理性)。 性情(disposition/Gesinnung)与品性(propensity/Hang): 性情这一概念能够说明意力的自由运用所包含的连续性与责任感,性情是持久型的意图,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hexis,但这种性情本身必须为自由选择权(意力)所采用,【它不是在时间中习得的】,它是准则之采用的【终极主观根据】,这种性情本身必须为自由选择权(意力)所采用;“并不是我们在时间中的一个特定时刻‘选择’了这种性情。相反,我们的性情是联合作用的结果,它源自我们所作出的自由的道德决定和我们所采用的准则”(p29);而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这而不是那,则是无法回答的,这是在强调“选择是自由的”,而不是倾向于神秘;性情不是发生在时间中,这是因为“说某事发生在时间之中,就是说它是由因果律决定的,因此它是不自由的。······性情不是由(自然)因果律决定的,相反,它来自我们的自由”(p30);康德把根本恶描述为一种“品性”,它是意力的败坏。 生理品性与道德品性: 生理品性是自然的,是属于因果律范围内的,所以没有善恶可言;而道德品性是自由的,向恶的品性就内在于意力的道德能力,“除非我们【自由地】采用恶的准则,否则,不存在道德的恶。采用恶的准则的意力在因果律上仅仅受它自身的决定;它【自发地】显示了我们的自由”(p35,由此可见,那种规训、建构话语批判,有为施恶者开脱的倾向,因为它把恶的源头诉诸规训者、建构者,而当规训者、建构者被唯心化,其实就成了无处诉诸),康德证明“真正的自由【不受任何】(自然的)因果作用的制约”(p35)。 康德引入根本恶的概念,意在说明“为什么(从实践的观点看)我们会偏离对道德法则的遵循”(p39),他在说明“意识到道德法则的人类有时(自由地)背离了道德法则”(p39)。 【无条件的道德责任】 康德从未在“人类都负有道德上的职责与责任”上作过妥协,他坚决相信:“不管这种品性怎样深深根植于我们的人性,对我们所作的恶负有责任的,不是这种品性,而是我们的自由意力”(p52);康德反对集体责任的观念;康德的“采用道德准则的终极主观根据是无法探究的”显示了他的智性诚实。 【第二章 黑格尔:精神的医治?】 在黑格尔那里,宗教与哲学的对象是同一个(永恒真理),差别只在于它们关注神的方式的差别;黑格尔对于无限与有限的看法是,无限并不是那种完全不同于有限的东西,“真的无限就是内在(自在,an sich)于有限之物。无限并不是对有限的‘超越’”(p64);有限与无限是同等源始的性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面对无限者(上帝),黑格尔并没有贬低有限者,而是宣称有限性的环节是多么的必要”(p67);上帝与世界之间没有本体论的分歧,“在【超验性】和【内在性】之间【没有本体论的分歧】”(p68);此后黑格尔左派就开始用人道撤换上帝:“如果没有本体论上的超验性,如果‘上帝’变成彻底内在于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之物,那么,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就能完全摈弃‘上帝’这一能指,把我们自己限定在对人道的谈论上”(p68);有限与无限是【辩证的关系】,“有限在真的无限中同时就被否定、证实和扬弃了”(p69);作恶就意味着“我与普遍者隔绝开来,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把自己独特化”(p75);分裂(恶之所在)是一个必要阶段;“作为分裂和自我断裂,恶的爆发不仅是人性形成的一个必要阶段,而且在这一自我断裂中,已有一种对于和解的期待,对于恶的扬弃的期待”(p76);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是一种神义论,因为他企图在【恶的表象】与【上帝的实在】之间达成和解;真正的无限在黑格尔看来是一个自我意识与上帝共有的统一体;黑格尔并不是说恶会得以清除,“被扬弃之物总是被予以保存”(p83);黑格尔对恶的分析并没有涉及恶的具体历史形式,“黑格尔对恶的复杂分析与我们对世界上的恶的经验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p86);黑格尔实际上认为“精神医治自身,不留丝毫疤痕”(p88),但这反映出黑格尔的辩证思想有限度,我们不可能相信扬弃与和解,但同时作者也认为不能完全拒绝黑格尔,他所关注的是“为【恶的实存】作证成”(p90),“如果拒绝按照恶所呈现出的样子来接受恶,拒绝用一种使我们在恶面前无能为力的方式来把恶具体化,这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黑格尔主义的做法”(p91),这其实是一种积极地与恶抗争、与恶对峙的任务;本雅明和阿多诺挑战了黑格尔的扬弃与和解:“有一些伤口留下了永久的疤痕”(p91)。 【第三章 谢林:恶的形而上学】 谢林旨在承认“恶的现实”,肯定恶的本体论地位,挑战了“恶的存在是善的匮乏”这种说法;自由必然伴随着恶,这是一种恶的形而上学,进而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将恶的现实归于‘无限的实体’——亦即归于上帝”(p95),这是神义论所避免的结论(这种做法很像Gnostics的复兴,恢复恶的本体论地位,也就有了两个上帝的可能);用“肯定哲学”代替黑格尔的“否定哲学”;一个博爱的上帝怎么可能是恶的现实的起源?谢林的答案是“在上帝之内肯定有某种上帝自身所不‘是’的东西”(p98);谢林要克服二元论,而试图发展一种【分化的一元论】,自然与精神之间没有界限;重要的区分是【根据】(ground)与实存(existence)之间的区分,“上帝必须在他自身之内具有他的实存的根据”(p101);所以存在的根据与现实的实存区分开来;谢林认为,秩序、形式是表面,“无规则的东西存在于深处”(p102);“理性是从非理性的东西中生出的”(p103);谢林试图避免两个极端:绝对的二元论和无分化的同质一元论;并且他反对通过否认恶的现实而调和善恶的伪解决方案;现实的实存与上帝的自我启示联系起来:“上帝因为他自己的自我启示而【需要】人类”(p105);谢林的上帝不是自足的上帝,这体现了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唯独在人类那里,存在着两个意志(向善的意志和向恶的意志)的碰撞或冲突”(p107);在上帝那里不存在原则的二元论,而只有一种【潜在的二元论】;谢林比康德更激进,他认为在自然与精神之间,或者说在因果必然性与自由之间没有鸿沟;恶变成实在是由于“颠倒了根据与实存的原则”(p110);只有在人类身上才会发生善与恶的斗争;在上帝那里,则是实存的根据先于他现实的实存;谢林的视野更宏大,“根本恶(深入到根部的恶)以宇宙论的黑暗原则为根据,而这一原则是无规则的、无意识的、混乱的并且总是危险的,这是人类永远无法完全掌控或制服的原因”(p115);他强调,“要成为完整的人,我们就必须带着激情与热力参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p116);这不是非理性主义,而是认识到人类理性的脆弱,他是理解我们人类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深刻洞察发生在人类灵魂中的剧烈斗争。 注:笔记仅涉及全书第一部分,即德国观念论部分(康德、黑格尔、谢林) |
精彩图文
 顾禹安苏柔(苏柔顾禹安)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顾禹安苏柔(苏柔顾禹安)全文阅读-笔趣阁
顾禹安苏柔(苏柔顾禹安)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_顾禹安苏柔(苏柔顾禹安)全文阅读-笔趣阁 (番外)+(全文)顾禹安苏柔(苏柔顾禹安)精彩小说-小说苏柔顾禹安全文无删减版免费阅读
(番外)+(全文)顾禹安苏柔(苏柔顾禹安)精彩小说-小说苏柔顾禹安全文无删减版免费阅读 萧慕瑶苏璟屹免费阅读-(萧慕瑶苏璟屹)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苏璟屹萧慕瑶)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
萧慕瑶苏璟屹免费阅读-(萧慕瑶苏璟屹)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苏璟屹萧慕瑶)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 经典小说戴上性感的绿帽,师妹从此无敌了无广告小说免费阅读鹿呦呦全章节免费阅读
经典小说戴上性感的绿帽,师妹从此无敌了无广告小说免费阅读鹿呦呦全章节免费阅读 (鹿呦呦)戴上性感的绿帽,师妹从此无敌了小说免费阅读-小说推荐戴上性感的绿帽,师妹从此无敌了精彩章节在线阅读
(鹿呦呦)戴上性感的绿帽,师妹从此无敌了小说免费阅读-小说推荐戴上性感的绿帽,师妹从此无敌了精彩章节在线阅读 流年深深深几许(周容川阮流苏)最新免费阅读-流年深深深几许小说在线阅读(后续+全集)
流年深深深几许(周容川阮流苏)最新免费阅读-流年深深深几许小说在线阅读(后续+全集) 周容川阮流苏(流年深深深几许)全文免费阅读_流年深深深几许全文阅读_笔趣阁
周容川阮流苏(流年深深深几许)全文免费阅读_流年深深深几许全文阅读_笔趣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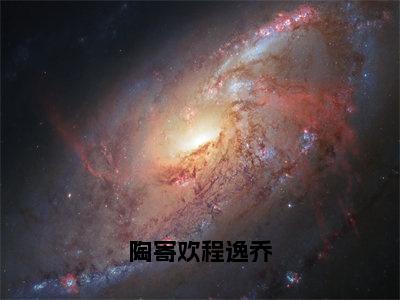 陶寄欢程逸乔全文(陶寄欢程逸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陶寄欢程逸乔)陶寄欢程逸乔最新章节列表
陶寄欢程逸乔全文(陶寄欢程逸乔)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陶寄欢程逸乔)陶寄欢程逸乔最新章节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