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ent of Literature经典读后感10篇
|
《The Event of Literature》是一本由Terry Eagleton著作,Yal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40.00,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读后感(一):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前言 《文学事件》前言 伊格尔顿 著 陆钓雪 译 文学理论在这二几十年来已然不再时兴,所以像这样的书也就日益罕见了。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实而感到谢天谢地,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来读这篇前言。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很难预见到符号学、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之类的理论会在三十年后对于学生来说会陌生得如同外语。总体说来,上述的理论都已经被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性问题和文化研究这曲热点四重奏推搡到了角落里。这对于保守的理论的反对者们来说可不是什么温暖人心的好消息。毫无疑问,他们盼望着理论的堕落预示的应该是一切复归初始状态。 当然,后殖民主义、种族问题、性问题和文化研究不是和理论毫无瓜葛的,而且它们也不会因为理论的堕落就变得过时。应该说,它们是跟随在“纯”(pure)或曰“高”(high)理论之后而爆发的,并且多半将它们的先驱置之于身后。事实上,不只是置之于身后,说是取而代之或许更为恰切。就某些方面看来,这种发展是受人欢迎的。大量理论主义的形式(尽管蒙昧主义不在其列)被弃如敝履。如今普遍占据主流的是从话语向文化的转向——从某种程度上抽象的或纯粹的方法向对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有人会鲁莽地称之为现实世界的调查研究的转向。一如往常,这里有赢家,也有输家。分析吸血鬼或《恶搞之家》①似乎没有像研究弗洛伊德或福柯那样富有知性上的益处。此外,正如我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所论述的一样,“高”理论不断地失去人心和政治左翼命途多舛的衰退也是休戚相关的。②这些思想蒸蒸日上的年代也正是左派如日中天、强健有力之时。而随着理论的日趋式微,伴随着它而悄然消逝的还有激进的政评。在其最鼎盛的时候,文化理论针对社会迫使其面临的状况提出了引人注目且野心勃勃的问题。今天,政权比往昔都更加全球化和富有权力了,“资本主义”这个词很少会去弄脏那些忙于庆祝和将自己向差异性敞开的或是汲汲于分析僵尸的人们的香唇。而这一点正是对于这个体系的权力的证明,而非与之毫不相干。 然而,本书对于文学理论也暗含了的一种指责。除了最后一章外,我大部分的论证引用的与其说是文学理论,毋宁说是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物种——文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文学理论家对于这类话语漠视地太过于频繁了,并且这样做导致了他们又将自己置于老掉牙的欧洲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陈腔滥调的争辩的角色之中。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文学理论从前者焕发而出,那么文学的哲学则在后者的致敬下而诞生。并且最佳的文学哲学在专业知识和严谨苛刻的程度上也与一些文学理论在理智上的宽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于这些文学理论还会将一部分理应处理的问题(例如虚构的本质)未经审视地遗留给别的阵营。 相反,文学理论在理智上如此之甚的保守和羞怯与文学哲学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文学理论还常常致命地缺乏决定性的批评鉴赏能力与富有创造性的胆识。如果说理论家们穿的都是开领衬衫,那么文学哲学家们(不论如何都肯定是以男性为主)则大多是打着领带登场的。一个学派表现得好像从未听说过弗雷格,而另一个学派则显得似乎他们并不知道弗洛伊德是谁。文学理论家们趋向于急速地转换虚构作品的真理、参照、逻辑形态等问题,而通常文学哲学家们则对于文学语言的结构特质表现得极为迟钝。近年来分析哲学与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之间显示出了一种古怪的(而且确乎没有必要的)关联,这当然不符合过去那些从事于这类思考的学者们的情况。 对于激进分子而言,他们倾向于质疑诸如“文学能有定义吗”之类的问题。油尽灯枯而又无视历史的大学教师就是这样的。当然啦,不是所有对于定义的尝试都会遭到质疑,当谈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或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之时,激进分子之中的绝大部分人一定都会同意定义的有效性的。恰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时而需要定义,时而不需要。这里面也有一种危险的反讽。在大多数文化左翼看来,定义是应当留给保守的专业学者的过时腐物。而那些学者们确实颇为无辜,因为当涉及到艺术与文学的定义之时,他们也持有着反对的意见。令学者们孜孜不倦、动力满满地去给出定义的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通过定义他们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定义是无用的。 当发觉他们投身于其中的起点,竟然是一段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讨论,读者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乃至于灰心丧气。引用乔伊斯式(Joycean)的措辞来讲也许是由于我体内经院哲学的腐臭所致,这也正好解释了我在本书开头的趣味之导向。我在天主教的背景下被抚养长大,此外我被教育说不能不相信理性分析的力量,况且后来我又从事于文学理论的职业,这些方面也肯定都与我的兴趣息息相关。甚至于有些人或许可以把我对于文学哲学的兴趣归因于我在牛津和剑桥的盎格鲁-撒克逊避难所里过分地虚度了我的光阴。 不过你不用成为一个前天主教徒或者前牛剑教师也可以领会这种境况的奇妙所在,那就是文学系的教师们和学生们习以为常地使用诸如文学、虚构、诗、叙事之类的词语,却对于探讨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无能为力。就算不说是令人震惊吧,文学理论家起码也奇怪得就像是那种见到一个胰脏能够认得出来但却无法解释其功能的外科医生。另外,有太多重要的问题在文学理论中被撂在一旁,而本书则试图着去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将从思考事物是否具有普遍的本质来开始。这自然与一个人到底能否讨论“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接着,我将探究“文学”这个术语在今天通常的用法是什么,然后检验这个我将其置于中心的词汇的每一个特征。这其中的一个特征——虚构性(fictionality)就足以复杂到需独立出一整章来探讨之。最后,我将转向文学理论的问题,追问它那各种各样的形式是否可以归结出相同的特征来。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这本书提供了文学(至少到目前为止)究竟是什么的合理的解释,并且第一次关注到了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的相同之处。不过我不是一个不谦虚的人,所以我不会这么说的。 我很感谢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ar)、瑞切尔·朗斯代尔(Rachael Lonsdale)和保罗·奥格雷迪(Paul O’Grady),他们都对我提出了富有智慧的批评和建议。同时我也要感激我都儿子奥列佛·伊格尔顿(Oliver Eagleton),他与我探讨“假扮”(pretending)的概念并且使得我修正了许多至关重要的观点。 T.E. 注释: ① 中译者注:《恶搞之家》(Family Guy),美国福克斯电视公司自1999年起开播的一部无厘头风格的戏剧卡通片,到2014年已经连载到了第十三季。——脚注皆为译者注,尾注皆为作者注。 ②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2003), Ch. 2. 译者说明: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一书的中文译稿,我最初完成于2015年年初。当时刚开始读研浑身是劲,从某一位教西马的老师处得知此书尚未有中译本时便跃跃欲试,一边请求那位老师帮我联系出版社和版权方,一边自己埋头苦译,苦中作乐。在2014年年末的时候,研一寒假,我基本上完成了译稿。那时候祖父突然去世,给我带来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打击。我也未将伊格尔顿附在书末的尾注译完,现将原注附在文后。也是因为自己初来乍到,不了解版权方面的复杂性,导致自己在翻译完之后才得知这本书的中译版权已为河南大学出版社所购买。这都是自己的无知所导致的教训。所幸河南大学出版社终于将要出版阴志科老师的译本,我很乐观其成,阴老师是伊格尔顿研究专家,我相信他对这本书的投入比我更多,也相信他的译本在任何方面都将比我的草稿来得全面。选择在此时此刻的“一方读书会”公众号连载这本书的拙译,纯属是为了给自己的过去一个交代,好让自己投入到接下来的学习以及另外几本著作的翻译工作之中,让过去真正的得到翻篇。译笔草就,水准不高,读者朋友如有任何问题和指正,还请不要吝啬。 ——译者 陆浩斌 丁酉年九月十八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读后感(二):从生产到阐释:伊格尔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从生产到阐释:伊格尔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 陈飞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伊格尔顿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显示了其从《文学理论导论》以来的理论重心由文化生产维度到读者阐释维度的转向。在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以“阐释策略”为批评视角,以“意义/力量”和“文本/身体政治”为主要范畴,融合了精神分析与政治批评,认为这两种批评理论都是同样地寻找无意识的祛伪式批评。同时,伊格尔顿立足于后现代语境,以美学与身体的双重矛盾为解剖对象,提出了建立一种后现代新身体学的马克思主义构想。 关键词: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阐释策略;精神分析;新身体学 伊格尔顿近年来广泛关注文化理论,但其2012年出版的《文学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似乎提醒我们,在后现代快感与多元的市场逻辑下,他并未忽视经典文学艺术所表征的价值意义,只不过其理论重心由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化生产转向了以读者阐释为主的文本解读。他以“阐释策略”为批评视角,以“意义/力量”和“文本/身体政治”为主要范畴来综合精神分析与政治批评,认为这两种批评理论都同样是寻找无意识的祛伪式批评,同时立足于后现代语境,以美学与身体的双重矛盾为解剖对象,提出了建立一种后现代新身体学的马克思主义构想。 一、从“审美意识形态”到“阐释策略”:伊格尔顿进入文本的两种方式 “审美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最为人熟知的文学理论概念,在其1990年出版的《审美意识形态》中,他以康德的认识论和审美判断的二元理论为跳板,分析了“审美”和“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阈下的特征。审美作为人类经验对更高级的世界的反映,为“个别的主体和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范式”[1](P90-91),审美“表面上是对世界的描述,但实际上是情感的隐秘的表达方式”[1](P85)。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其所指是对某些必要的情感内容的遮蔽,也就表征着言说者与他者社会的互动关系,因此“审美等于意识形态”[1](P91)。只是与特拉西对观念知识的研究有所不同,意识形态经由审美而成为一种有关实践的理论。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研究伊格尔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贯穿了伊格尔顿从1976年的《批评与意识形态》到2012年的《文学事件》前后近四十年的思想历程。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他分析了爱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奇》中的蛛网意象,认为小说内部的意识形态问题被巧妙地移置为美学形式本身的问题,其形式与意识形态的结合“既避开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单纯形式主义,又避开了庸俗社会学”[2](P114)。同样的,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强烈谴责了庸俗马克思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未能把握住形式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主要媒介,所以它就更不能理解形式何以能在文学想象的建构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帮凶的。”[3](P220-221) 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密切相关的是他的文化生产理论,即文学艺术是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在197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这本小册子中,他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认为“作家不只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且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4],艺术生产就相应地成为了一种社会生产形式和实践活动,间接地构成了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这并非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同作为生产的艺术之间的牵强联系,而是着重突出了艺术对科学的、理解社会的经验和意义的传达。此后,伊格尔顿相继出版了《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批评的功能: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和《文学理论导论》等著作,在保持对文化生产问题的关注中,将批评的重心从作者转向了读者,这种理论重心的转向相继表现在《文学理论导论》和《文学事件》中。 在《文学事件》一书的序言中,他袒露了其写作目的并非是大言不惭地“为文学到底是什么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也不是“为了讨论所有的文学理论的共同点而故意招徕关注”[3](Pxii)。基于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他在该书第五章集中阐发了他提出的“策略”(strategy)概念。由于中英文思维的巨大差异,中国文学理论界很少有人使用“策略”这一抽象的批评术语。不巧的是,他至始至终都没有给“策略”下过清晰的定义,只是认为“没有一个单一的特性可供所有的文学理论共享,但是却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可以说明一系列文学理论的特性”,这个概念就是“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策略”,它是万能的,几乎适用于一切文学理论。[3](P169)在伊瑟尔的接受理论的影响下,他认为“策略将作品与读者联系起来,这才使得文学作品得以存在”[3](P186),是读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对文本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的加工和重组。因此,策略在伊格尔顿那里就成为一种批评视角,它不是某一个固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而是读者以某种视角来进入文本的方式,采用这种批评方法就意味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用一套策略去解释另一套策略”[3](P185)。 虽然这种阐释策略是以接受理论为基础的,却与伊瑟尔有很大不同。伊格尔顿认为“没有一套概念能向我们展示作品的全部意义,解释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正确方法这种想法是错误的”。[5](P92)作品的真正含义并不是不能解读出来,也不是可以任意解读的,我们的解读需要找出支持我们对作品的解释的某些特征,“这类特征有很多而且不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5](P93)。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格尔顿的阐释策略带有方法论的意味,而伊瑟尔的接受理论则偏重于对读者作用的认识。 这种策略更进一步地在他对本雅明的革命式批评的解读中得到娴熟的使用。他将读者的阐释策略扩展到了作为生产者的作者那里,认为在移情作用中阐释具有一种策略性的力量。他以布莱希特为例,认为剧作家可以根据观众的反应来改写自己的剧本。因此,作品本身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劳动”,在他看来就“不是对外在于它的历史的一成不变的反映”[3](P170),而是在同外在现实的忽远忽近的游离关系中建构了自身。这一看法沟通了文学与世界、内部与外部两个时空。作为一种象征行为的叙事,马克思主义代表了这种阐释策略的希望:“作为策略,艺术作品属于必然王国,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受较少限制的象征王国。作为运动,艺术作品预示着自由王国的到来。”[3](P179) 阐释策略以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批评视角为主,同时连接了作品和作者,最终指向现实政治。在《文学事件》的最后,他以阐释策略为切入点,从两个方面回答了一个困扰理论家很久的问题:艺术是自律自足的,还是对外在于它的世界的某种指涉?首先,他声明“文学作品是作为对其自身问题的一种解释而被掌握的”[3](P223)。其次,他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只关涉到一系列的阐释策略而不关涉作者的意图,“艺术作品是否是以压抑的形式达成的意识形态的合谋无关紧要,它是人类实践的范例,因而也是使人类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的一种探索” [3](P224)。阐释策略的提出,或许更加确定地表明了伊格尔顿的理论重心朝向读者对文本解读的转移,而从审美意识形态到阐释策略的理论历程也显示了伊格尔顿对待文学批评的一贯立场:“所有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6](P213) 二、两套批评范畴的提出:意义与力量,文本与身体政治 伊格尔顿以阐释策略为批评视角,力图在《文学事件》一书中用无意识理论综合精神分析与政治批评。首先,精神分析被弗洛伊德认为最初是作为一种阐释的技术而诞生的,它脱胎于从病人身上发现其所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东西。伊格尔顿糅合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认为精神分析作为一种阐释学,是一种“对人文科学不满的话语”[3](P210),更是一种倾向于分析病人的莫名的无休止的欲望的阐释策略。精神分析所要研究的正是“欲望被言说进而成为言语时所发生的一切”[1](P265)。在谈到移情作用的时候,他又认为精神分析在提供对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上接近于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即“梦文本类似于意识形态:二者都是象征行为,这种象征行为代替了一种与心理的或政治真实之间的‘不可能的’冲突”[3](P218)。无意识的愿望就是一个潜文本,它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解释就是对文本的重写进而达到对潜文本的重写,甚至是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外在历史和意识形态。[7](P71)。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阐释策略来看,精神分析可以解释政治行为,政治批评也可以引入心理学维度。 伊格尔顿又从现象学那里借来一对概念以表达言说与被言说、未言说之间的矛盾,这对概念就是“意义/物质”(meaning and materiality),而“意义与物质是绝不可能没有矛盾地并置在一起的”[3](P214),于是他改造了这对概念,用“意义/力量”(meaning and force)来表达精神分析的话语所具有的力量,这种话语又被同时看作是语义领域(semantic field)和权力争夺的场所(cockpit of contending powers)。[3](P210)如此一来,精神分析的话语便可以相应地分为“语言/身体”,这种供精神分析研究的身体布满了能指。因此,精神分析就将身体当作文本,认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脚本,其症候或能指之半显露半隐藏的意义需要被破译出来,但是,文学批评却反过来将文本视作身体一样去解剖,揭示出其中的意识形态主题。在精神分析看来,无意识或欲望“是对真实的歪曲,是对叙述连贯性的破坏,是对一个能指与另一个能指的混淆”,以至于“为了其不正当的目的而挟持了言语”。[3](P210)这样的真实说到底只是一种虚构的陈述,真实并不在场,它仅仅作为一种述行话语而存在,这类话语充斥着权力和欲望,需要我们运用阐释策略对其运作程式进行修辞学式的细致分析。精神分析和文学艺术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叙述,前者的“精神分析治疗室”和“谈话疗法”洞悉了经验背后的真实,由于自我扮演着力求道德的角色,超我既是超道德的更是残酷的,梦文本经过润饰作用就已经被梦者修改过了,后者也通过诗或戏剧等形式与真实间接联系着。所以无论是精神分析还是文学批评,文本都是“生产伪陈述的一部机器”[8](P165)。 其次,政治无意识则是一种关于将历史文本化的叙事范畴,“正是在查找那种未受干扰的叙事的踪迹的过程中,在把这个基本历史的被压抑和被淹没的现实重现于文本表面的过程中,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学说才找到了它的功能和必然性。”[7](P10)詹姆逊从社会阐述欲望又从美学阐述政治,辩证地分析了历史与真实的关系,他用渐近线图式形象地表达了历史无限逼近却永远无法抵达真实的矛盾。他认为,真实“是对抗欲望的东西,是欲望的主体了解希望破灭所依赖的基石”[7](P176),而这种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主要是依靠无意识的叙事或幻觉,它是“一种不稳定的或矛盾的结构”[7](P172)。伊格尔顿以弗洛伊德的释梦为例,在对梦文本的解读中,发现了无意识力量与身体的冲突,梦文本实际上是扭曲的、有所遮蔽的、经过了置换的,这种无意识力量导致了对真实的严重歪曲。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伪装的愿望实现,它同时包含了真实的愿望和对这种愿望的想象性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类比了精神分析和政治批评,认为精神分析和政治批评都是对无意识的寻找,旨在对文本表面的真实祛伪。 作为文化生产理论的倡导者,伊格尔顿受到马歇雷《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一文关于“文学作品是对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想象性解决”[9]的启发,认为“与其说文学作品‘想象性地置换了’真实,不如说文学作品是一种生产,它把某些已经生产出来的关于真实的再现形式生产成想象的客体”[10]。这种再现形式的生产源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11],这种克服表现为法律、政治、宗教、艺术或哲学。这个思想被马歇雷、詹姆逊和伊格尔顿继承下来,而怎样克服就牵扯到了精神分析的程式。但是,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无法为现实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它只是将问题表现出来,为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提供一种途径,因为“一旦人类冲突都没有了,那么文学也会随之消亡”[3](P217)。【关于“想象性”的问题,请参见拙文《意识形态的想象性功能》http://www.douban.com/note/592148996/】基于这样的阐释策略,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精神分析和政治批评的实践功能得出如下结论:“获得更加互惠的和平等的爱的方式是精神分析的目标之一,也是革命政治的目标之一”[1](P287),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友爱政治学。尽管伊格尔顿不断强调读者的解释作用,但是他从未放弃从文本到文化的理论探索,在后现代革命热情衰退的语境下依然流露出一种政治关怀。 三、建立后现代“新身体学”的马克思主义构想 关于建立一种“新身体学”的构想早在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有所流露。他在该书的开篇就声明“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审美构成了“朴素唯物主义的首次冲动”,这种冲动是长期以来身体对理论专制的某种无言的反抗。[1](P1)他坚持美学的政治功能,认为美学是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它是一种真正的解放力量,主体通过内在感性的自律重建了个人与他者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把权力置入每一个主体的内部,从而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这意味着对美学的执着探索既可以从自律性的维度对自我进行一种深度的调整,有利于对社会生活的异化的有效预防,又可以从他律性的维度对资产阶级或者任何一个制度体系保持必要的清醒。也就是说,伊格尔顿通过对资产阶级美学及其政治领导权的解构,激活了作为理论话语的美学,赋予了美学以政治实践的功能。既然实践是人类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主要方式,那么身体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对世界发挥作用的途径,是进入世界的方式,是世界围绕其有条理地组织起来的中心点”[12](P17-18)。这种以身体为核心的美学阐释策略在后现代语境中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同美学一样,身体被伊格尔顿认为是充满矛盾的流动式能指链,这成为后现代身体的显著特征。首先,对身体的逐渐关注伴随着革命政治的衰退:“过去的列宁主义者现在是彻头彻尾的拉康主义者,每一个人都从生产转向性欲倒错。格瓦拉的社会主义让位于福柯和方达的身体学。”[12](P81)其次,后现代的主体是分裂的、松散的、杂乱的,是没有基础的,拥有着尚不成熟的能力,其从事重大实践改造的能力已经在对于确定的知识的信仰的破灭下一并退化。然而正是这种被后现代主义充分关注的身体,否定了企图均质化的等级制度,符合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怀疑。身体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现在饱受嘲笑的启蒙主义理性更基本更内在的认识方式”,而且身体本身也是“一种被复杂地代码化的东西”。[12](P82)这就是说,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后现代思潮同化并利用,对身体的关注本身就具有政治性。 基于美学的政治功能和身体的后现代遭遇,伊格尔顿呼吁我们有必要建立一种“新身体学”:在晚期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里——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道德正义等问题被证明是此刻难以解决的,人们总是会将注意力转向一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12](P22)。在这种新身体学说中,身体或将成为首要的阐释策略:“有了身体就有了准备影响世界而非与世界隔绝的方式”[5](P160)。正如上文所述,身体是对革命政治的某种替代,新身体学因而也就在语义层面上不说是替代了政治行动,至少是对政治失败的疗伤和补偿。 后现代展演着身体的狂欢和轻浮,它迷恋无论是物质的还是意义的快感,与此同时,面对内在的力比多和外在的劳动实践的双重逼迫,身体也是严重压抑的。不过,伊格尔顿却认为这种压抑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因此,他批驳了后现代身体的过度时髦,并义愤地评论道:“吸引人的是性……在某些文化圈里自慰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社会主义已彻底输给了施虐受虐狂。在研读文化的学生中,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的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味索然。”[5](P4)他从后现代思潮中看不出积极的政治意义,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的嘲讽只是为了表明他的义愤和担忧:后现代思潮容易让人们回归到琐屑的日常生活,进而有可能丧失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 但如果对后现代的身体不屑一顾,则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因为这种异化的存在具有本质属性,是身体从自身的角度对后现代的否定。伊格尔顿抓住了后现代身体的这种矛盾从而对身体表示赞扬,他认为身体的独特性表现在“它是一个中心,从这个中心它们可以组织成为意义重大的构想”,身体是具有创造性的,具有改造自身的能力,同时“它能够从制造它的东西中制造出某种东西”,它的最高代表就是语言。[12](P84-85)可以看到,他对后现代新身体学的构想不仅仅是以美学和身体政治理论为基础的,还透露出语义学的哲学支点:首先,“语言是本质的”并且“同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着”[3](P10);其次,“人类意识乃是主体与他者在行为上、物质上和语义上的交往”,语言是一种“物质生产手段”,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6](P114-115)既然语言代表了身体的某种创造性,语言就理应成为新身体学的重要武器,话语的批判力量也就构成了对身体政治的影响,以种族、阶级和性别为焦点的身份认同问题或许也就能够得到更具有实践力量的解决而不是一味地纸上谈兵。 尽管伊格尔顿的理论重心已经向读者这一极转移,但他的立场从未发生根本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及其现实政治的终极指向一直贯穿在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中。他始终坚持一种文化生产的美学,在以一种独特的视角进入文本的阐释策略的指导下,高扬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弥合了形式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口,从语言到身体,从文本到政治,一种以审美解放为目标的后现代“新身体学”正在崛起。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65. [5]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郭国良,陆汉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65. [9]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C].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49. [10]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C].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06. [1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12]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From Production to Interpretation: Postmodern Turn of Terry Eagleton’s Theory CHEN Fe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Terry Eagleton’s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2012 shows his focus turning from literary production theory towards hermeneutics since his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esthetic ideology production theory, Eagleton takes the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as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the “meaning/force” and “text/body politics” as the main categories to integrate psychoanalysis with political criticism, holding that both critical theories are the same to find unconscious anti-pseudo type criticism. Based o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Eagleton puts forward a Marxist conception of postmodern and neo-body science with the dual contradiction of aesthetics and human body as the anatomical objects. Key words:Terry Eagleton;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psychoanalysis; neo-body science ---------------- 本文完成于2015年2月。 本文刊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Q&dbname=CJFDLAST2016&filename=HBGD201605013&v=MjMyMTBacEZpamtVcnJOTFMvTWFyRzRIOWZNcW85RVo0UjhlWDFMdXhZUzdEaDFUM3FUcldNMUZyQ1VSTDJmWk8=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读后感(三):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第一章: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 第一章: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上) 伊格尔顿 著 陆钓雪 译 《文学事件》 让我们从一个看似毫无意义的转向说起吧。如同许许多多理论上的争辩一样,实在论者和唯名论者的辩论也是古已有之的。①而在中世纪的时候,这场辩论兴盛到了轰轰烈烈的程度。若干杰出然而持有相反信念的经院哲学家们排成长队以兵戎相向。是否如那些紧跟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的脚步的实在论者所宣称的那样,一般的或普遍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还是像唯名论者所坚信的那样,我们把概念强加在这个世界的头上,而事实是,任何真实的事物在这个世界里都已经是不可简化地独一无二了?文学或者长颈鹿性是否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真实世界中存在?还是说这完全只是依赖于思想之中的观念?长颈鹿科是否就是从一群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生物中抽象而出的思想?抑或这类物种和这群个体即便不是以同一种方式但至少也是同样的真实的存在? 对于唯名论者这一派来说,这类抽象是在个体事物产生之后而形成的观念;而在实在论者看来,这类抽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个体事物的,正是抽象的观念的力量使得个体事物成为其所是。没有人曾亲眼目睹过什么鳄鱼性,但相反的是,有人见到过这只或那只有鳞甲的野兽在沼泽中晒着日光浴;然而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者会急着来提醒我们,也没有人亲眼见过一个社会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福克斯电视台②或者英国银行实际上并不存在。 在此,折中之法或许是切实可行的。伟大的方济各会③神学家邓·司各脱(Duns Scotus)提出了一种温和的或者说是合理的实在论。他认为本质在思想之外是有现实存在的,但想要完全成为共相(universal)则必须借助于思维。④托马斯·阿奎那应该会同意他的观点。共相并非属于物质实体,正如如罗杰·培根(Roger Bacon)⑤之类的极端实在论者所说的那样,但也并不只是虚构而已。假设共相在思想之外没有真实的存在,它们至少使我们能够得以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这些共同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在事物的“自身之中”。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⑥则持有一种比司各脱远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共相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逻辑形态。⑦司各脱的思想则并没有局限于此,但他对于特殊者却有着一种明显的嗜好,最闻名于世的例子就是他的门徒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⑧对于他的书信中的“此性”(thisness)和个体性(haecceitas)的观念的引述。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倾向于将物质实体视为一件事物的个体化原则之所在,而相对照地将事物的形式视为一种别的共有的实体,灵巧博士(the Subtle Doctor)⑨能洞察每一个造物使其成为独一无二、内在固有的自身的动态原则。而他对于特殊性所感的兴趣,则可以从他对耶稣基督这个人的方济各式虔诚之中得到部分的解释。 个体性将具有共同本质的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截然区分(没有两片雪花或两道眉毛是一模一样的),这正显现了一个存在者(a being)的终极实在,并且令人了解到了上帝也只有一个。这也就是说,要把握一件事物超过其概念或共同本质的地方——一种不可化约的特殊性,不能依赖于理智上对一个客体的反思,而只能靠对于其清晰在场的直接领悟。在一种名副其实的思维革命中,如今的个别事物对于人类的思想来说成为了明白易懂的本身(per se)所在。司各脱被他的一个评论家称之为“个体性的哲学家”(philosopher of individuality)。⑩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⑪认为这名中世纪的方济各会士是所有最伟大的形而上学者中的一员,并赞美他是“第一个阐明了个体的存在”的思想家。⑫我们长途跋涉地经过了自由主义、浪漫主义、阿多诺对于一个客体的概念的非同一性(the non-identity)原则,还有后现代主义怀疑共相作为诱饵是为政治上的不谨慎者而设的陷阱等等诸多道路。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⑬的评价非虚,我们可以以后见之明来看出唯名论者热情洋溢地把特殊性当作了“西方文明史的至要转折点”。⑭ 与唯名论者大相径庭的是,实在论者倾向于认为我们无法从对于个体的特殊性的把握中来获取知识。在一个种属的科学的对面,并不存在什么一颗个体的大白菜的科学。在阿奎那的观点里,思想无法把握物质实体——事物的个体化原则。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个体化的事物。对于阿奎那来说,这就是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功能,它涵盖了对于具体特殊性的非理性认识,并且它也正是所有美德的要点所在。⑮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的感官知觉式的或曰肉体式的阐释,我不得不说这种观点和阿奎那后来对于肉身的沉思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久以后,一种研究感官知觉特殊性的科学将作为对于抽象普遍主义的反驳而诞生在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它的名字叫作美学。⑯美学是作为一种非常自相矛盾的物种而开始它的生命的,它是研究具体的科学,它探寻我们肉体生命的内在逻辑结构。差不多在两个世纪之后,现象学也将会发起相似的研究计划。 对于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实在论哲学家来说,一件事物的本质即其存在的基本原则。而正是因为借助了这种存在性,该事物也参与进入了上帝的生活。在这种实在论的理论观点下,上帝在众生(beings)的核心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通过上帝之无限的分享,一件事物二律背反地得以成为其自身。黑格尔后来对这一原则进行了世俗化的扭转:精神(Geist)使得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之所是,而因此有限也组成了无限。还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信念认为如果一件事物能够完全自发自主且具有自我同一性,那么这几乎也二律背反地表明了无限者不会认知任何超过它自身的东西,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无限者之外并不存在任何东西。 大千世界气象万千,所以人们谈话的方式自然也是差异丛生的;所以人们才需要去了解事物本质的秩序,就像后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明白如何在给定的语境之中来玩语言游戏(language-game)。多元主义与本质主义走到了一起。但如果事物真有给定本质的话,我们很容易发觉它反过来会对设计这种本质的神自身的力量造成一种限制。上帝总是可以凭着他的智慧去选择不去塑造海龟或三角形,因为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创造的任何事物都不需要有什么必然性。任何存在物都可以是无端无由的。这意味着任何事物也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同时也就不会持续在思想扭曲其可能性的问题里相形见绌了。有一点至少对于人类来说是真的,那就是他们会意识到自身之不存在的可能性,一般说来,也就是对于死亡的畏惧。而同样真切的是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的困扰纠结,因其令人毛骨悚然地或欣喜若狂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偶然性。一件事物成为世界上的存在,这在阿奎那及与其持同样观点的人看来属于上帝的馈赠,而与逻辑推理或者铁一般的必然性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关于爱的问题,与必然无关。造物的原则应该从上帝的爱之中去寻找。这和世界如何飞离地面毫无瓜葛,这类问题是留给科学家而非理论家的。事实上,阿奎那认为世界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起源。他的精神导师亚里士多德也持这种见解。 鉴于海龟和三角形真实存在着并有着其确定的形态,而上帝也不得不和我们一样必然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不能异想天开地像笛卡尔以为的那样去决定2+2=5。在制造了自己的宇宙之后,上帝被迫地居于其间。当涉及到事物本身所存在的方式之时,他不能表现得像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暴君或者骄奢放纵的摇滚明星。上帝是一个实在论者,而不是唯名论者。他被约束在自己所创造的本质之中。 在一个经验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会趋向于用数不胜数的理由来怀疑这类共同本质。关于一种事物用理智比用感知去把握更能令人理解的看法一定会冒犯经验主义者的偏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可以感知察觉的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根本就没有任何本质可言,那么上帝的最高统治权也就真正得到了保障。他可以让一只海龟引吭高歌《天降横财》(Pennies from Heaven)⑰,只要这种场景能取悦于他就行。任何事物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愿意”(quia voluit, because he willed it)。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dt)⑱对这一观点的描述恰如其分,他在阐释哲学家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⑲的思想时说道:“上帝是终极性的绝对权威。整个世界与在这个世界中的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由他所独家代理的。”⑳颇成问题的是,权力的随心所欲为万能的造物主敷上了一层神秘莫测、令人费解的黑暗色调。他成了一个行事套路与我们凡夫俗子全然不同的隐匿的上帝。用理性来观照他简直不可思议,他的存在无限偏离他自己的创造物,就好比一个远离芸芸众生的名流一般。他是激进的新教徒的上帝,而不是《新约·约翰福音》里那个把自己的帐篷驻扎在我们之间的上帝。㉑ 通过从现实中净化本质或共性,你能够减轻阻碍的程度,从而更温和地去靠近权力。除此之外,肯定也有别的类型的更具有成效的反本质主义,但是他们的胜利却通常忽略了某些东西,即此原则同时也合法化了自己时代的人类统治权。久而久之,会有人以上帝或人道之名来谋取他人的性命或篡夺他人的王位,他们会日趋无所不能,而本质却无处可躲。只有在耗尽这个世界的固有价值的过程之中,你才能寻找到慢慢消解这种建立在计划之上的阻力。对事物真正的统治权,就像弗朗西斯·培根知道的那样,包含了对他们的内在的特性的知识;但这也可能会导致在对于特殊性的尊重的问题上产生分歧,马克思称其为使用价值。 如果我们可以把自然搞成任何让我们感到愉悦的巴洛克式的奇形怪状。一股冒险的狂妄自大的气息必将铺面而来,人类亦将耽溺于自身拥有无穷无尽的权力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在现代性的后期阶段,人性会被自己将之推上舞台的法则、权力、习俗所取缔,而这些东西也将取代人的地位而扮演着最高价值授权人的角色。所有反基础主义者都会因迷醉于自己的辩护色彩而缔造出一种新的类型的基础主义。他们强调着自己在做的是一种我们的铲子连挖都挖不到的最最基础的工作(称呼其为文化、结构、语言等等)。在如此这般地扭转了上帝的最高统治权之后,人类大厦终将因其自身的话语而坍塌毁灭。 让我们暂时地回到现代性的节点上吧。只有通过削除感官的纹理和琐细的稠密到一种数学般精准的薄度值,用我们自己测量和计算的策略去定义各方各面的特征,把世界的粘稠浓密化约到我们的精神可以再现的程度之内,造物才能够剥去差异性而后完完整整地被交付到我们的手里。事物如今皆以其如何对应于我们的规程和技术而被定义,可我们的认知却对它们本身如何完全忽略不计。我们或许不能像上帝一样理解事物,但至少我们可以去了解我们自己生产的客体,劳动的行为在此显现出了一种全新的重要性。以为我们行使着巨大的改革力量的想法属于新教徒式的乐观主义,正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操纵着一切的做法也是属于新教徒式的操心。这个世界会因此而显得好像是莱姆(Lem)的《索拉里斯星》(Solaris)㉒里的海洋,它将不再具有任何特征,令人不得要领而最终变得莫名其妙。难道自由的获得必须以现实的丧失来作为代价?不管怎么说,自身如果没有任何本质可言——不过是力量的一点机能、感觉印象的堆积体、纯粹的现象实体、一个非连续性的过程、无意识地露出头来——那么谁才是全世界变革的原动力?而它又到底服务于谁? 在这出荒凉无望的剧本里,一个绝对主体遭遇了一个纯粹偶然发生的世界。反本质主义的另一张面孔是唯意志论——权力的扩张与收缩正如操控它的主体一样,它最终是其自身存在的结局与理由。它也是其自身存在的基础与动因。但如果这个世界对于权力的繁荣旺盛毫无任何确定性可言的话,那么对于权力的有效行使又如何能有一个确定的基础呢?如果现实是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那它又何以长久稳定地使我们得以完成自己的目标,并且让我们对权力持有一种自由而乐观的看法呢?不管怎样,在行使对于其本身毫无意义的一堆物质的统治权之中,到底又有何乐趣可言呢?我们掌控的支配权和管辖权越多,相应的我们的空虚也越多。因为现实不再是有效组织的结构化,不再厚重地沉淀着意义重大的特征与机能,不再像以前那样阻挠着我们争取自由的行动;反而如今成为了我们自由所带来的空虚的象征。是不是除了同义反复,除了一个物种用一只手授予这个世界的它的另一只手来作为意义,我们一无所有? 奥卡姆的威廉之类唯名论者认为实在论者混淆了词与物,而保罗·德·曼㉓之类的文学理论家们却觉得真正混淆的人是唯名论者自身。因为当我们说“林荫大道”或者“山毛榉”之时,我们倾向于假设有可以与此术语对应的可确认的实体存在。实在论在此是一种具体化。何况,既然我们永远也不能真正地理解事物独一无二的个体化存在,实在论由此也可以被看做一种怀疑主义。奥卡姆却大异其趣,他将所有在主客体之间的概念中介一笔勾销,确信我们是通过理智直观来领会特殊实体的。通过直观我们可以真正地理解实体存在——在即刻中最充分地去领会——其自身。对于后来的经验主义来说,共相不过是对于离散的个体状态的归纳罢了。它们不再表征着一个客体的内在真理,也就是说这类客体将停留在所谓的神圣授予的天性的表现之中,而不再能够被进一步地归纳总结。故而我们需要一种分析事物表现的话语,这种话语并不导向荒谬的形而上学概念。这种话语将被我们所有人所知晓,因为它的名字就叫作“科学”。 与阿伯拉尔㉔和马克思相同,阿奎那也坚信所有的思考都早已预设了共相的存在。其他方面暂且按下不表,这位天使博士(The Angelic Doctor)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个反经验主义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1844)中曾提到过,必须要有抽象的或一般的概念才能够“上升”到具体之物。在这个观点中,具体物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自明(self-evident)之物;将它视作一系列的决定因素(有一般的也有特殊的)的汇合点可能更为恰当。具体之物在马克思这里是异常复杂的;为了能够用思想来认识具体之物,马克思觉得调动那些在他看来远为简单的一般概念是不可避免的。总体看来,理性主义者是从一般演绎到个别,而经验主义者是从个别归纳到总体。 并且,马克思确信共相不只是为了方便而设的观点,共相是实实在在的世界大花园中的一部分。例如,后期马克思将他所命名的“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ur)㉕当作资本主义生产的组成要素。如果没有这一要素的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将会瘫痪。这种看法可谓言之成理。马克思在其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olosophical Manuscripts, 1932)中曾说过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个体,他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是以特殊性的形式参与到“类存在物”(species-being)之中,而正是共同本质赋予了这一个体化为自我本身的过程以力量。在这种唯物主义者的人类本质观念里,个体与共相并未被当作截然相反的要素来看待。 这场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的争辩无休无止,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他们对待可感的具体之物的态度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正如它也是个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这还是个抽象推理在循序渐进的经验主义者的世界里到底占据了什么地位的问题。真实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只有眼见才为实?阿伯拉尔宣称实在论在其强调一般本质之时也泯灭了事物之间的所有差别。在实在论者的眼里,所有的奶牛都是灰不拉几的。安瑟伦(Anselm)㉖则相反,他谴责了唯名论者并说他们是“如此之深地陷入在了物质的幻象之中以致于不能自拔”。㉗在这类柏拉图式的观点中,唯名论者沉浸在了他们感官的饲料槽里,着迷于直觉的即时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对于现象的实质是那样地短视,根本无法获取任何高瞻远瞩的思想。就是因为这个根深蒂固的缘由,热血激昂的实质主义者柏拉图才在他的理想国里流放了所有的诗人。他们被感官的音乐所攫住,以至于失掉了上升到抽象理念的高贵。现代的诸多文学类型也遭遇了相同的宿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解释了他们对于文学理论的仇恨心理。 针对实在论者的抨击,唯名论者尖锐地反驳道,我们不应该从理性主义者写的所谓第一原则和形而上学本质中来读懂这个世界,思想本该更为直率与纯粹。在唯名论者看来,理性主义者和本质主义者讲的好像他们在未经审视这个世界之前就能够理解现实为何物。事实上一个人理应遵照培根式的风格,从个别的事实中归纳出一般的科学法则,而不是(高度理性主义风格化的)反其道而行之。一般的或普遍的范畴扼杀了事物“此性”的生动活泼。从邓·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到吉尔·德勒兹㉘,这里有着一道崎岖不平的路径。在德勒兹这个司各脱主义者对于一般范畴厌恶腻味的自由主义论调里,其实存在着一种与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狼狈为奸的勾结关系。在尼采式的言辞中,这些绝对的思想只会被看作是暴虐无度,它们横行霸道地在具有独一无二身份的对象的头上逞着淫威。后现代主义继承了这类偏见。这类偏见的卑贱的起源,乃是基于中世纪晚期对于恣肆而专断的意志的狂热崇拜。 相反,黑格尔和卢卡奇则认为,对本质的认识可以赋予个体化的对象以自由,使其掀开隐秘的面纱并通向真正的自然本性。从美学维度来讲,他们的思想包含着饶有兴味的双重运作,首先是从一系列个体经验中萃取出一种类型或本质,紧接着又再次为它披上特殊性那光泽明亮的外套。同理,浪漫主义想象的作用也是将现象转化为其本质的象征,而在如此做的同时又充分保留着它们那感官的外表。这种双重运作有时又显得颇为棘手。因为假设经验现实是通过一种幽灵般的事物聚合体而组织在文学文本中的,隐秘地在典型和本质中理解境况,那么现实就很明显地渗透着确定的必然性。也许这就是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在他观察时曾蓦然想到的:艺术是“一道从偶然通往必然的走廊”。为了抑制难以把捉的可能性,作品似乎在宣称事物是受其内在本质所压制的,所以也就只可能会有某一具体的形态而无其它可言。而如此对于其他可能性不言而喻地否定的姿态,正是一种颇具典型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之类似的,认为诗使得言语文字的构思的具体化到了不得不如此的确定性程度——“正确的语序上的正确的词汇”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导向压抑符号的可能性的危险,则是另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语言是“本质化的”或“现象化的”,只有在其与一种实在的关联完全紧密无间之时,仅在此特殊情况之中,它才显得像是图像而非符号。 注释: ① For this de bate in general, see M.H. Carré, Realists and Nominalists (Oxford, 1946); D.M. Armstrong, Universals and Scientific Realism, vol. 1: Nominalism and Realisim (Cambridge, 1978); and Michael Williams, 'Realism: What's Left?', in P. Greenough and Michael P. Lynch (eds), Truth and Realism (Oxford, 2006). ②译注:福克斯电视台(Fox TV),隶属于世界娱乐行业巨鳄之一的福克斯娱乐集团,推出了不少风靡全球的王牌美剧,例如《越狱》(Prison Break)、《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等。 ③ 译注:方济各会(Franciscan),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由1209年意大利的方济各(Franciso Javier, 1182-1226)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而成立,提倡托钵行乞的清贫生活。 ④ For Scotus, see M.B. Ingaham and Mechthild Dreyer, The Philosophical Vision of John Duns Scotus (Washington, DC, 2004). More advanced studies are Thomas Williams (ed.),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Duns Scotus (Cambridge, 2003) and Antonie Vos,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uns Scotus (Edinburgh, 2006). See also Alasdair MacIntyre, God, Philosohy, Universities (Lanham, Md., 2009), Ch.12. ⑤译注:罗杰·培根(Roger Bacon, 约1214-1293),英国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实验科学的前驱,主要著作有《大著作》、《小著作》、《第三部著作》和《哲学研究纲要》等。 ⑥ 译注: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1285-1349),英国经院哲学家,圣方济各修士,邓·司各脱后来的论敌,以复兴唯名论著称。他认为思想并非对现实的衡量,将哲学与神学截然分开。其主要著作有《逻辑大全》、《辩论集七篇》等。 ⑦ For a magisterial study, see Gordon Leff, William of Ockham (Manchester, 1975). An equally informative discussion is to be found in Marilyn Adams, William Ockham (South Bend, Ind., 1989). There is also some useful material in Julius R. Weinberg, Ockham, Descartes, and Hume (Madison, Wis., 1977). ⑧ 译注: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Manley Hopkins),英国诗人,他在写作技巧上的变革影响了20世纪的众多诗人。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使用的“跳韵”(sprung rhythm),这种韵律更关注重音的出现而不是音节数量本身。其主要诗作有《茶隼》、《上帝的伟大》等。 ⑨译注:灵巧博士(the Subtle Doctor),指司各脱。 ⑩ Antonie Vos,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uns Scotus, p. 402. ⑪译注: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 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自然科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 ⑫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ed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 1 (Cambridge, Mass., 1982), para. 458. See also James K. Feible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Charles Sanders Pierce (Cambridge, Mass., 1970), p. 55. ⑬ 译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 ),当代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黑格尔与现代社会》(Hegel and Modern City, 1979)、《自我的根源》(Source of the Self, 1989)、《现代性之隐忧》(The Malaise ofModernity, 1991)和《世俗时代》(A Secular Age, 2007)等。 ⑭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2007), p. 94. ⑮ See Fernando Cervantes, 'Phronesis vs Scepticism: An Early Modernist Perspective', New Blackfriars vol. 91, no. 1036 (November, 2010). ⑯ See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1991), Ch. 1. ⑰ 译注:《天降横财》(Pennies from Heaven),1936年由麦克雷欧德(Norman Z. Mcleod)导演的歌舞喜剧式同名电影中的歌曲,获第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提名奖。 ⑱ 译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dt, 1888-1985),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倡导决断主义(Dezisionismus)和国民法治国(Rechtsstaat)1933年加入纳粹党,主要著作有《北极光》(Nordlicht, 1916)、《宪法学说》(Verfassungslehre, 1928)等。 ⑲ 译注: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 1638-171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十七世纪笛卡尔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真理的探索》(1675)、《论对上帝的爱》(1679)等。 ⑳ Carl Schmidt, Political Romanticism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6), p. 17. ㉑ There is a useful discussion of this theological view in 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3), pp. 152-5. ㉒ 译注:《索拉里斯星》(Solaris),前苏联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1921- )创作的科幻小说,小说以一个被神秘大洋覆盖的为背景,演绎了人类寻求知识和生死相爱的科学神话。该小说于1970年和2002年分别被苏联导演塔尔科夫斯基(Andrel Tarkovsky)和美国导演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两度搬上银幕。 ㉓ 译注: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比利时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杰弗里·哈特曼(Jeffrey Hartman)并称为“耶鲁四人帮”。其主要著作有《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 ㉔ 译注: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 1079-1142),法国神学家、哲学家,人称“高卢的苏格拉底”,主要著作有《神学导论》、《自我认识》等。 ㉕ 译注:“抽象劳动”(abstract labour)是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中的关键概念,是指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没有质的区分而只有量的区分。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但却不等同于价值,它在凝结到商品之中后形成价值。 ㉖ 译注:安瑟伦(Anselm,1033-1109),罗马天主教经院神学家、哲学家,他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并对上帝做出了“本体论论证”。 ㉗ Quoted byCarré, Realists and Nominalists, p. 40. ㉘ 译注: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 1925-1995),法国居翘楚地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欲望哲学的研究非常深入,并由此出发而攻击一切中心化和整体化思想。伊格尔顿曾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 2011)一书中直呼其为尼采的门徒,由此或可看出伊格尔顿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矛盾纠葛。德勒兹主要著作有《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 第一章:实在论者与唯名论者(下) 伊格尔顿 著 陆钓雪 译 《文学事件》 唯名论正如弗兰克·费瑞尔(Frank Farrell)①所论证的,表征着对世界的祛魅,同时也依稀地预示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劫难。②造物不再如往昔那样有所畏惧了。我们不难发现的是,这个由修道院外的俗人、经验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科学理性主义者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抱有着作为人类历史的经纪人的统治欲),在晚期中世纪的世界里自有其渊源可溯。让我们简短地一瞥这世界何以如此演化的某种缘故吧。上帝在阿奎那看来并不是与人类和真菌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之上的存在,而是远在那盖世无双的高空之中。许多理论家会选择存疑的是,如果非得说上帝是一种存在,那么他也是与他所创造之物完全不成比例的存在。所有事物之存在都有它们的可能性的极限,而爱则支撑着它们存活下去,上帝在这个角度来说也是高深莫测的。他不能被我们判定为具有特殊性的万物之一。宗教信仰者可能在很多方面都犯了错,但当他们控告说发现了世界上并不存在另一个实体即所谓的上帝之时,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错。 邓·司各脱的观点与阿奎那相比可谓是截然相反,他将上帝看作是与蜗牛和双簧管同等的存在,只不过更无限地不同与卓越而已。这样讨论所带来的悖论性效果是通过宣告了蜗牛与双簧管的紧密关系,而把造物主推挤出了这个世界。上帝与我们处在同一种本体论地位,但却又不可思议地更深一层。一道裂缝恰如其分地横卧在了崇高的造物主与他那实在的造物之间。而阿奎那的上帝是超验的也是无所不在的,这意味着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人类的理性所把握。这还意味着,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的事物都会在它们最内部的存在之中留有自身的印迹。简而言之,这个世界是神圣的。世界在它的作者那里是明显的可读性文本(lisible text)③。这位作者飞舞翱翔在他的艺术品所触手难及的天空中,但他也因此变得逐渐难为人类的理性所琢磨,而只能通过信仰去彻悟;至于有限的人类,因为他们纯粹是偶然性的,也就不可能像论及阿奎那一样去论及上帝。当上帝宣告他离我们远走越远之时,也正是现实的文本潦草地越来越难以辨认之际。 一个悖论油然而生。如果上帝将他的绝对统治权硬行地施加在了他的造物的头上,并且他还碾碎了独立的生命使得其不能够存活下来以亲眼目睹上帝自己的胜利。那么这世界岂不是恰恰因了他主宰万物的在场而显得空洞无物了吗?④这个出人意料的真相揭露的是人类与世界那所谓的初与终的完全不合理性与不合人性。到如今,万物都为其自身而存在,不再是那万能的主的晦涩的寓言了,他们也都能够成为普通人认识的对象了。假设上帝远在那片信仰的国度里,和实际价值没有任何关联,那么一个全然世俗的世界也将会有诞生的可能。这一俗世将把自己神圣的王冠交到科学的手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解放。理性的研究不必再屈膝于被神圣所授予的本质。哲学可以砍断那条紧紧拴在神学上的锁链。并且既然人类已不再受亘古不变的本质所束缚,他的确可以成为现代性的自我塑造、自我决断的历史代理人了。被剥去玄虚光环的事物终于可以被拿来为人类的幸福和利益所用了。进步的观念不再会显得不虔诚。我们可以介入大自然的法则之中,而不必将之奉若神明,我们大可以以此来为我们自身所属的物种谋福利。在人类的研究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超乎底线的。我们确定物质世界是完全自主的,它并不是什么另一片版图的朦胧象征。它不再被当做一个神圣庄严的文本,也不再是一串神秘难解的字码或在自身外部另有所指的能指符号。 与此同时,这场涌向现代性的运动也表征着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某种中世纪后期思想里那性情无常而又专制的上帝演化成了现代新纪元中自我决断意志的模范。与全能之主一样,这种意志的所作所为皆以其自身为王法;而不同于全能之主的地方是,它用那绝对的统治权威胁着万物的生命。在此意志下任何想法都有它自己的理由和目的(因为它天生就预设了应该去做什么)而决不会显得随心所欲或不合理性。其实这种观念在司各脱那里就早已经萌生了。对奥卡姆来说也是一样,意志是最高统治者。意志并不卑躬屈膝地臣服于理性,因为它肯定早已把我们该选择怎样去做的理性给驯养地服服帖帖了。自从意志变得无所不能之后,理性也早已终止了它的道德智能,转而把自己降格到了纯然工具性的地位。现在,理性只不过是激情、兴趣、嗜好和欲望的女仆罢了。这条由司各脱和奥卡姆开辟的道路将到达其现代主义者的里程碑:尼采式的权力意志(will-to-power),接着,径直通向后现代文化的纪元。在那里,主体的意志将被极度地耗尽与去中心化。⑤尽管如此,兴趣、权力和欲望依然是后现代主义者思考的基础,而理性对它们的批判性反思则会被显著地化简殆尽。理性对于后现代主义者和对于某些学院人士来讲一样,将会限制兴趣与欲望,所以决不能够被运用于基本的判断之中。在后文里,我们将会在一些文学理论中看到有关此事的暗示。我指的是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⑥的作品。 托马斯·阿奎那对意志有着极为不同的看法。在他眼里,意志不是任意而为且独立自主的权力,而应该是对美德的顺从,是偏向于一件事物与生俱来的价值的气质。意志因此是开阔的生机盎然,随时准备着行动起来,而很难符合于后来的西方思潮所描述的那种模样。“将意志付诸实践(对于阿奎那来说)”,费格斯·克尔(Fergus Kerr)⑦写道,“更像是赞成那些富有最强烈之欲望的美德,而不是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温不火甚至顽固执拗的事情……(意志的实践)与欲望、赞同、欢欣的顺从等概念结盟,一言以蔽之:与爱同行。”⑧ 唯名论者也因其对个体的极度关心而在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⑨的历史中扮演了毁灭性的角色。在这种看待事物的观点下,个体是自主存在的,而个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则是非本质的、契约性的和非结构性的。这远没有萝卜之间的交往关系那么显而易见,严格地讲,甚至连说他们之间存在交往关系这种话都显得有些牵强。正如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s)⑩曾经说过的那样:“正是唯意志论者的神学观授予‘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哲学要点那最初的渊源。”⑪想改革这样的状况需要一种社会整体(social totality)的责任心;而唯名论者在嫌恶共相与抽象这一点上也应当受到谴责。还记得那个不明是非的撒切尔夫人(Ockhamite Margaret Thatcher)在观察之后得到的所谓的结论吗?她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 在经院哲学范畴的约束下,万物之存在的解脱被证明为某种程度上的自掘坟墓。科学也许会研究经验主义的特殊性,但它也常常限制了对感官肉体的关注。科学在将存在从形而上本质的统治内解放出来之时,又将其归纳入了同等抽象的普遍规律的序列之中。一边唾弃之,另一边又将其原原本本地叼了回来。一种现代的现象首当其冲地抵制着抽象性,其名曰艺术。⑫作为浪漫主义的宝贵遗赠,它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对于感官具体性的占有。 这就是文学类型何以都趋向于为特殊性身先士卒的一大理由。它们之中的绝大部分都本能地感觉到了抽象性的倒人胃口。唯一能唤起它们一小部分热枕去赞同的一般范畴只有“文学”自身而已。只有当“文学”范畴本身遭到侵犯之时,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辩护士们才会立刻挺身而出,求援于抽象概念。⑬“文学”唤起如此之大的诽谤中伤的原因之一是这个习语自身几乎就是一种矛盾修辞法。文学这样不可化简的具体之物又怎能成为抽象研究的对象呢?艺术不是偶然之特殊性的最后避难所吗?艺术不是妩媚动人而又不落俗套的细节吗?艺术不是率性不羁的冲动吗?艺术不是剥除一切教条约束的紧身衣并打碎一元化幻觉的特异姿态吗?它的重点难道不是要挣脱空谈理论者的专横、对现实的系统扼要概括、政治行动的纲领、正统观念的酸臭、官僚和社会工作者那扼杀灵魂的日程表吗? 大多数文学类型在此意义上来说是唯名论的。不论其为老派的自由主义也好,还是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也罢。“远离理论与概论的运动”,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的小说《网之下》(Under the Net)⑭中的安娜黛恩(Annandine)谈论道,“朝向真理的运动。所有的理论化都在漂浮。我们必须因势利导而此情势即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性。”我们可以从现代文学评论的年鉴中发现这个论点被成千上万次地复制再生产。即使列宁(Lenin)也提出过一种类似此论的版本。理论是一件事,而艺术或生活则是另一件事了。一个人简直不需要去指出安娜黛恩的陈述本身就是理论化的宣言。事实上,在默多克的小说里蕴含着不胜枚举的抽象反思。默多克将其塞入了形形色色被宠坏了的圣人、牛津的波西米亚人、衰退的空想主义者和中上阶级形而上学家的口中。能够知道为什么任何人的状况可以既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性又仍然能为人们所理解一定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们何以能够谈论绝对与其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个性?又是靠着什么概念(而所有的概念又都不可避免地是一般性的,比如“这个”、“唯一的”、“不可模仿的”和“说不清道不明地与众不同”等等)表示说我们可以明确此类的情势状况? 人们应当注意到,这是引人注目的新近艺术观。热衷于一般性而对个体性感到无聊嫌恶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绝对会对这一现象感到奇怪。许多前浪漫派艺术家必定也会深表同感。这是种存活了两个多世纪一点的艺术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当时人们也已经很难制作出那类意义上的艺术品。很难进一步弄清楚这到底是怎样被澄明的,比方说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吧,他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对抗此类自由人道主义者的虔诚。它依靠某种灵巧的手法或看似自由浮动且特殊化的错视画(trompe l’oeil)⑮般的幻境来秘密地引入一个更“典型的”或类属的虚构、人物、情境的系列。同样模棱两可的是它借此能在何等程度上烛照文学现实主义的伟大血统。作家当中为我们所知的沉溺于此种策略的其中一个就是艾丽斯·默多克。这两种文本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被设定为严格的对称——都柏林中显然是随意的某一日与暗中却严密的系统化荷马时代的潜文本——构建了对经典现实主义的一种戏仿(parody)。那迷失于偶然性与概念框架的如今将被撕开并且成为自身的漫画,成为仅仅是讽刺性的、与他者联合一致的自我假想。这一小说所具有的形式亦是对其自身的道德声明。现实主义也许表现得像是在与迷途的特殊性谈情说爱,但他忽略了一些尤为至关重要的形式方面的问题。 存在主义的浪潮方才衰退,唯名论的最后一曲历史乐章就由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书写了下来。像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这样的思想家都极为反感一般概念、共相原则、告密的本质和总体化的政治纲领。除此之外,他们应该不太像是那批中世纪晚期经验哲学家的后嗣。当托尼·班奈特(Tony Bennett)⑯说需要的不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是一种文学们的理论:具体的、在历史上特定的和唯物主义的文学们的理论”之时,他是以一名左翼唯名论者的身份来说的。⑰难道我们真的要假设在这些不同作品的实质内容之间没有任何重大的关联?它们必须被严格地认定为分散而独立自主的存在?假若真是如此,我们又何必把他们都叫作文学呢?无论如何,又是否能有具体的、在历史上特定的和唯物主义的对诸如死亡、悲伤和苦难之类的共相的研究呢?(一些人也许会认为不是共相,而正是这样的探究、广布和执着,被我们称之为悲剧。)⑱ 班奈特想要为美学整体挖掘坟墓,质疑其为唯心主义与泯灭历史。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一大伙的艺术哲学家会兴高采烈地认可他的文学观。并且他们恰恰是以美学家的身份来这么做的。他同样也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当文学的范畴在历史上反复无常之时,它的一些成分——比方说虚构,或者诗——将会成为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文化。最终更惹人注目的事实是:努尔人(Nuer)⑲或丁卡人(Dinka)⑳的讲故事会与皮科克(Peacock)㉑或索尔·贝娄(Saul Bellow)㉒的讲故事完全不搭界,还是两派在跨越如此之大的文化鸿沟后仍能有达成可辨认的文学形式的共识?历史也许在连续性和共同特征那里,正好也与差异性和间断性具有同等的动力。即便是最动荡混乱的历史纪元也会在断裂和革命的同时显露出永恒性与持存性。并非如班奈特之类的唯名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共相”就一定意味着“不合时宜的超时空”。共相正如个体,自有其特殊的实质性的历史。 这里存在着一种不同寻常且又危如累卵的反讽。后现代主义理论向科学、理性主义、现代的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投射去了猜疑的目光。但它毕竟根深蒂固地有赖于唯名论蔓生的那个年代,且不论其对于此一学说所处的历史背景是多么的无知。就此意义而言,后现代主义理论不过是局部地摆脱了它自以为已然彻底抛在身后的东西。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没有摸索到唯名论与权力之傲慢的隐秘的姻亲关系。它没有发觉本质主义如何在暗中发挥着保护存在的完整性以免受统治欲望的持续高压的作用,使得我们不必在其淫威之下怯懦而圆滑地去亦步亦趋。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一惯保持着认为有关本质的学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应受谴责的普遍主义精神。算不上是后现代主义的偶像之一的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㉓肯定会着重强调这一点的。 调动从一类文化到另一类文化的分类图表作为参照应当是值得的。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㉔中,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宣称在部落社会中的客体对象也许会被指派为一个具体的范畴,而这并不应该简单地归因为它们拥有固定等级的限定属性,还因其奠定在这群人类生存群体的象征性联系的基础之上。正如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㉕所言:“一种分类(在这样的社会里)并不都具有一个总体逻辑在内,而是有一连串的‘局部逻辑’(local logics),因为所有物品中的各与各的关联都基于非常不同的评估标准。成问题的规则可谓不计其数而又形形色色,且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都截然不同。”㉖不管这一切看起来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并没有被逼着在分类框架的共相绑缚和纯然差异之间二选一。上述观点对我随后将阐释的“文学”问题有着一定的影响。 并非所有的共相或一般范畴都一定是暴虐压迫性的而只有承认一切皆为差异性和特殊性才算是站在了天使这一边。一个人若是对共性有所反感,他只需要在对待事物的问题上少一些堂皇的普遍化即可。对于像福柯这样的唯名论长(archnominalist)㉗来说,所有的分类都是暴力在暗中为害的形式。而对于像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这样更富有理性的灵魂来讲,为了确定的目标而将个体团结起来或许是有利于他们的解放的。这并不能表明他们在别的各方各面也完全相同。 也许可以树立一个更进一步的观点了。本质主义几乎总是被哲学家们当作本体论的命题来对待——事物存在的本质问题。但如果我们以道德内涵的问题去取而代之呢?如果人类的“本质”是我们爱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呢?有人或许会说,既然现在我们将转向差异与特性的问题上去了,爱会在解决明显的对立面时被涉及到,至少在它突然出现在人性层面的时候。反正“爱”这个词一般不会在文学理论式的讨论中被接纳,何况它在上下文的语境中又是如此坦率到简直不得体的程度,我将唐突地舍弃这个讨论就像我唐突地接触它一样。无论如何,这个观点在思考到不可爱的现象诸如鼻涕虫或者螺丝刀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可言。 注释: ① 译注:弗兰克·费瑞尔(Frank B. Farrell),当代英裔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主体性、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Subjectivity, Realism, and Postmodernism,1996)。 ② See Frank Farrell, Subjectivity, Realism and Postmodernism (Cambridge, 1994). ③译注:可读性文本(lisible text),法国著名解构主义社会评论家及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在其著作《S/Z》(S/Z, 1970)中提出的符号学概念,与可写性文本(scriptable text)相对应。罗兰·巴特以此二者来区分传统文本与现代文本,认为前者意义封闭而后者可由读者去添加乃至修改意义。 ④ A paradox noted by Conor Cunningham in 'Wittgenstein after Theology', in John Milbank, Catherine Pickstock and Graham Ward (eds), Radical Orthodoxy: A New Th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 p. 82. ⑤ For an excellent study of Scotus'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see Chtherine Pickstock, 'Duns Scotus: Hi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Modern Theology vol. 21, no. 4 (October, 2005). ⑥译注: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 1936- ),美国当代读者反应批评的重要理论家,他的“意义即事件”、“介绍团体”、“反对理论”等观点皆有深远而独特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为罪恶所震惊:<失乐园>中的读者》(1967)、《这门课里有没有文本?介绍团体的权威》(1980)等。 ⑦ 译注:费格斯·克尔(Fergus Kerr, 1936- ),当代英国神学家、哲学家,任教于牛津大学,阿奎那研究所(The AquinasInstitute at Blackfriars)领导人。 ⑧ Fergus Kerr, Thomas Aquinas (Oxford, 2009), pp. 69 and 48. ⑨ 译注: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二十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C. B.Macpherson)创造性地提出的批判观点,以此揭露了自由主义理论中自我的至高无上性和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并深刻剖析了自由资本将自我欲望化、社会工具化处理的内在缺陷。 ⑩ 译注: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s),英国当代激进正统主义神学家。主要著作有《神学与社会理论:超越世俗理性》(Theology andSocial Theory: Beyond Secular Reason, 1991)。 ⑪ John Milbank, The Future of Love (London, 2009), p. 62. For Milbank and his Radical Orthodoxy colleagues, Scotus really represents the moment of the Fall, a reading of him which has been strongly challenged by other scholars. He stands on the brink of a disastrous lapse into modernity - a lapse which is not for these commentators a felix culpa or Happy Fall, as it is for Marxism. ⑫ See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Ch. 1. ⑬ Not all of them, however. Graham Hough tells us in An Essay on Criticism (London, 1966) that we all know what we mean by literature even if we cannot define it (p. 9). The English do not need to bother with definitions, bearing as they do such knowledge in their bones. ⑭译注:《网之下》(Under the Net, 1955),英国小说家艾丽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的小说处女作,书名出自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Abhandlung, Logical-Philosophy Treatise, 1921)中的术语,意为语言如网,笼罩在五彩的世界上。语言既能反映现实,又能掩盖现实。该小说的特点是没有主人公。 ⑮译注:错视画,从古罗马时期流行而来的一种幻境画,立体感强而逼真。 ⑯译注:托尼·班奈特(Tony Bennett),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 ⑰ Tony Bennett, Formalism and Marxism (London, 1979), p. 174. ⑱ Tragedy in the artistic sense known to the West would seem to have no precise equivalent in Eastern civilisations, and thus is not exactly universal in scope. But its presence across a whole range of Western cultures and a lengthy time-span is notable even so. See my Sweet Violence: The Idea of the Tragic (Oxford, 2003), p. 71. ⑲译注:努尔人(Nuer),指苏丹境内和埃塞俄比亚边界上的尼罗特人牧民。 ⑳ 译注:丁卡人(Dinka),居住在苏丹南部的黑种部族人。 ㉑译注:皮科克(Thomas Love Peacock, 1785-1866),英国小说家、诗人,东印度公司官员,与雪莱是挚友并互相影响着对方的文学创作。其主要著作有《噩梦隐修院》(Nightmare Abbey, 1818)、《克罗切特岛》(CrotchetCastle, 1831)等。 ㉒译注: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当代饱负盛名的作家,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雨王汉德逊》(Henderson TheRain King, 1959)、《赫索格》(Herzog, 1964)、《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 1975)等。 ㉓译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论》(PoliticalPhilosophy, 1776)、《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Philosophy of Laws, Ethics, Economics, 1789)等。 ㉔译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Mind, 1962),法国结构主义人文学术思潮的主要创始人、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的代表作,此书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拉开了法国结构主义的序幕,宣布了对存在主义的全面挑战。 ㉕译注: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 1958- ),英国恐怖小说家,其代表作为《三角妖之夜》(The Nightof The Triffids, 2001)。 ㉖ Simon Clarke, The Foundations of Structuralism (Brighton, 1981), p. 191. ㉗译注:唯名论长(archnominalist),伊格尔顿自造的词,由前缀“arch”与名词“nominalist”组成。为了与段首谈到的“天使”(angel)相对应,伊格尔顿将大天使亦即“天使长”(archangel)的词缀引入“唯名论者”(nominalist)的词汇之中。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读后感(四):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第五章:策略(全书终)+译后记 1 现在是时候从文学自身是否分有一个共同本质的问题转移到对文学进行研究的理论上来了。如果真能有的话,文学理论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是什么衔接了符号学和女性主义,形式主义和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阐释学或后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 一种答案或许是它们都是理论。这就意味着它们至少具有一个(否定的)共同特征:经验主义或印象主义批评的一个共享的对立面。即便如此,理论性的与其他种类的批评之间的区别也是远远不够清晰的。可不能是前者运用复杂抽象的概念而后者则并非如此。所谓的非理论性批评一直都在采用此类概念(象征、寓言、性格、韵律、隐喻、净化等诸如此类)。只不过是它大多都停止去承认这些抽象的概念是什么罢了。有关性格、情节或抑扬格五音步的想法被期望为自明的,而无意识、阶级斗争和漂浮的能指则不然。这么看来,职责所谓的理论太过于抽象的批评家们倒往往是心眼太坏了,且不论他们是何等不知不觉的。也许他们可以言之凿凿地以其他理据反对它,但绝不能凭这一点。可能这些概念被文学理论家们在某种意义上使用地比其他种类的那些批评家要更抽象得多,或从非文学渠道上被采纳地太过度了。但这一点,同样,也是有待争议的。在何种意义上曲言法(litotes)[①]比反应迟钝的男性形象要来得更不抽象呢? 家族相似性模型看上去会同等地运用文学理论及其反对者。不存在什么单一的或成套的特征是一切文学理论所共有的。不管怎样,存在的只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一个重叠与交叉着相似性的复杂网络”。拿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容纳了无意识这一观点来举个例子吧。这显然是精神分析批评的看法,也(在为它所用的程度上)适用于相当数量上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但它在另一种方式上也适用于结构主义,对其而言的一部文学作品,尤似一个个体,通常无意识于支配自己的“深层结构”。语言,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评价道,有其为人所不知的道理。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语言又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包含了无意识,在能指无边无际的蔓延钻入任何可被阐明的话语以后——简单地说,“文本性”——从来都不能作为整体而被呈现在意识之中。至于政治批评譬如马克思主义,文本无意识变成了塑造自身及其根源的历史性的与意识形态的力量,而那必将无从得以自我认知。如果作品意识到这些力量的话,它也就不会以它所存在的形式而存在了。 现象学批评,相比之下,为无意识保留的空间很是有限,而符号学与接受理论也大同小异。虽然如此,这些方法与我们刚考虑过的那些之间还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方说,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属于同一个话语世界。家族相似性还可以被进一步扩展。现象学与接受理论同样强调了阅读体验的重中之重。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怀疑阐释学”(hermeneutic of suspicion)的概念既无关于政治批评又无关于精神分析批评。文学理论没有本质,但它也不是一连串随意组合的想法。在这点上,它类似于文学自身的现象。 然而,比这更胜一筹也是有可能的。所有这些文学理论或许并不具有一个单独的特征;但是有一个独特的概念却可以点亮它们大多数,虽说这个概念并不总是为它们自己所运用。这就是作为一套策略的文学作品观。既然这与种类如此之多文学理论都有所相关,我们在此最好还是稳妥而谦逊地称其为一种(几乎)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吧,一种在文学上等值于物理学家难以捉摸的TOE的理论。 如同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正是肯尼斯·伯克而非别人将此术语补充到了关键词之中,虽说伯克在今天大概算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批评家中被人忘却的最厉害的那一个。1恰恰是他教导我们将文学作品,其实笼统地讲也是语言,都考虑为对既定情境的策略性反应,故而其术语为仪式、戏剧、修辞、表演与象征行动(symbolic action),而其中统摄此批判哲学的词语则非戏剧主义(dramatism)莫属了。2我们所有最早的文学理论之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视悲剧为净化的一个象征行为;而尽管这一形式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但其名字自身,意为“山羊之歌”,兴许能表明它是基于另一个象征行为之上的一个象征行为,意即替罪羊的献祭赎罪。还有其它具有这般起源的文类。史诗和抒情诗作为口语行为而开启新生。讽刺诗是一次象征性剥皮。或许直到小说的出现,辅以大规模的印刷技术,文学作品观才以一个对象而非一个实践深深扎根于批判性思维之中。 可以发现杰姆逊他自己早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里就硕果累累地吸收了这些主打伯克式观念,在该书中他很是偏爱一种解释模式,它以一个双重姿态,既重写了文学文本又揭露了它自己来作为一个优先的历史性或意识形态浅文本(subtext)的重写。3而这一潜文本,可看作是对文本正文的一个反应,有其并不实际存在于文本自身之外的古怪品质,当然也不是某些“常识的外在现实”。它毋宁是事实之后的重构——可说是,著作本身逆向的投射。作品创设的历史性问题必须从它所给予的答复中读取出来。如保罗·利科所言,诸如《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或《哈姆雷特》之类的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家矛盾的投射也是它们解决方案的大纲”。4颇成悖论的是,文艺作品投射而出它本身内在的十足历史性与意识形态潜文本是一个策略性反应。而这一点,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文艺作品的一个精细循环或自我塑造的品质,此外还有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虚构的结构、言语行为的本质与诗性符号的特征。 倘若这是如此一个神通广大的模型,这主要归功于它带有包含文本与意识形态或文本与历史之间关联的复合视野。这些事物不再像在一些主流马克思主义美学里那样被把握为彼此坚守着反映、复制、对应、同源以及诸如此类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个单一象征性实践的选择性晶面。作品自身不被看作是一个在它之外的历史的一种反映,而被看作是一种策略性劳动(strategic labour)——一种令作品进入现实的方法,为了通情达理,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相含有,故而又阻挡任何头脑简单的内外二分法。杰姆逊写道为了作用于这个世界,作品是如何必然地以某种方式与世界相内置的,“它为了服从形式的转化而将内容纳入自身之中”。“我们于此所有的整个悖论就称之为潜文本,”他写道,“兴许归结起来就是,文学作品或文化客体,哪怕是破天荒头一遭创设出特有情境,而它同时也是对此情境的一种反应。”5 在关于伯克的批评的一篇较后的论文中。杰姆逊再度奏响了这一主旋律,写道如何“文学或美学姿态得以常常与现实保持某种活动关系……而为了作用于现实,文本不能单纯地让现实固执己见地处身在它自身之外,彼此隔阂而失却了生命力;它必须将现实汲入它本身的肌理之内。”“象征行为“,他进而说,“因而开始于生产它本身的语境并同时对应于它往回的浮现,以关照它本身的活动表现来做自我考量”,由此造成了如下幻觉,即艺术作品的情境是一种事先并不存在的反应——简而言之,除了文本什么都不存在。那么两个成问题的契机或方面就来到了这里,只不过在分析上有区别:那历史或意识形态现实自身,如今被相宜地“文本化”了,在文本运作的形式中逐步建立或“生产”;而这有变革能力的投射表达自身,在杰姆逊的语句中代表了“对应于新现实、新情境、从而也是新生产的文本积极活跃的、可谓有益的立场。”6 人们或许会视杰姆逊于此所描述的处理为人类普遍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人类在一个生冷而死气沉沉的环境下工作而只会在总已完备的“文本化”下,以数不尽的先前或同时的人类投射创设出如古本般地意义。总的说来,人类物种对境况产生反应而后它造成了它自己。它被它本身的产品所萦绕,就像偶或被他们所妨碍。如果世界对人类的奋进采取如此冷酷无情的阻挠,那与其说是因为它粗野而原始的地理,倒不如说是因为它已然被其他意义与活动所刻画定型。“劳动”一词本身就表明了世界部分对我们为其设计的反抗。现实,以一种杰姆逊式的口吻来说,就是那伤痛的。 可是,到文学作品这边情况就不一样了。当然,写作之事并非魔法般免于劳苦,但是唤起一个语境或潜文本的行为,还有对之产生影响的处理,同样皆为(劳动)实践的方面。就这来讲,文学作品展现了词语和世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团结一致,正如我们在言语行为理论那里所看到的一样。要是写作可以成为其它种类实践的一种取代,那它也可以成为对补偿它们的一个形式。杰姆逊这般措辞道:它是“一个行为的造诣及行为的代替者,一个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方式与对此类行动所具有的可能性的补偿,这一切皆在一夕之间”。7 那种弗洛伊德式错误的专业术语名叫行为倒错(parapraxis),意指一种搞砸了或替代了的行动或言说,并且这似乎是一种看待一般象征行为的富有成果的方式。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大概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优秀的散文家,他曾经在一篇论“虚言”的布道中控诉文学“几乎在骨子里”就是虚言,因为它展示了思想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在另布道一篇“论造诣之危险”里,他告诫道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凭借着从行为中割离出感受而使得我们的情绪无端受到刺激,故而在道德上是有害的。 象征行动,总而言之,看上去像是行动的一个残废、憔悴的形式,这就是纽曼之辈的圣徒的奇葩见解。我们离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相去甚远,尽管相比柏拉图对艺术的非难来讲还是要近那么一点的。文学的存在好像要依靠于某种对现实的缺乏或远离,这一不在场是其在场的重大要素。被称为精神分析的人类主体也可以这么说。仿佛作品会寻求对这一现实匮乏的补偿,那是所有象征实践的一个条件,依借将其更紧密地重获于语言之内;也就是说,在此特定媒介中回归本源。所有文学,如同所有语言那样,注定是永恒的歧义。它被迫在一个含有世界之丧失的媒介中再创世界,起码在感官的即时性层面上而言是这样的。象征是事物之死。就这一点而论,写作同时是人类堕落的一个符号与赎回它的一次尝试。 然而若文本在此意义上是次级与派生的,只不过是行动本尊的一个隐喻或取代,那它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全然现实化、充分完善化了的行动,它不会达不到现实因为它所忠于的现实不是别的而正是它为自己所组装的现实。古典文学作品正是以这种方式废弃了所有现实生活中的行动都会遭受的贻误与偶然,根除了意外从而以和和气气的形式与内容并结连理。既是取代又是补偿,象征行为由是把捉到了语言的某种引起歧义的效力与纤弱。一方面,语言不是别的而是字词。另一方面,它是最初促使人类行动成为可能的力量,正因为我们是语言的动物那一只来来回回摆动的手才会被视为一个告别的姿势。 认为文本是答案的想法不应被太过字面地读解。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的,并不普遍地持有针对问题的教科书式解决方案。我们不期待博尔赫斯(Borges)或奈保尔(Naipaul)的一部作品以一排欢呼雀跃的婚礼、恶人被空手打发走而善人被他们的国家奖励了大房子来终告圆满。在罗兰·巴特的术语意义上,倘使存在着愉悦(pleasure)的文本,以其彬彬有礼通融于我们规范性的假设,那自然也存在着迷醉(jouissance)的文本,从对它们的扰乱中断里收获恶意的、反超我式的(anti-superegoic)欢愉。典型维多利亚小说以和解的调子为结尾,这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设置也可以在其他事物中看到。“幻想的原动力,”弗洛伊德谈论道,“是未满足的心愿,每个单独的幻想都是一个心愿的实现,一次对未满足的现实的改正。”8在传统大团圆结局中,愉悦原则介入而柔化了现实原则的严苛,这般操作有时候被称之为喜剧。与之相反,典型现代小说,如雷蒙·威廉斯有一次所评论的那般,以主人公独自使他自己解脱出某些困境为结尾。 “没有什么文学在这个世界上,”罗兰·巴特写道,“曾回答过它所提出的问题,也往往是这一特有的悬置构成其为文学:亦即人们在问题的暴力与答案的缄默之间所运用的特别脆弱的语言……”9文本没有义务要像医疗诊断那样去有意地提供一个答案。它可能只是简单地对它所持有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反应,而没有一个文字上的解决方案。如果一部作品中同时具有解决一个问题的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途径,那作品中也会同时具有使其悬而未决的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途径。 弗洛伊德他自己也意识到一个心愿在我们本身的角度若是实现地太显眼、太完满则会令他者感到厌弃,虽说这在现代文学那里并不算什么紧迫问题。一个结局太恰到好处或太在意料之中会满足一部作品格式化的冲动只不过要付出瓦解其富有洞察力的现实主义的代价。这是因为幸福在现代算不得一个貌似可信的状况。甚至这个词自身都显得痿弱无力,唤起的无非是躁狂的嬉笑与走到了路的尽头的喜剧演员。在这幻灭的日子里一部喜剧的结尾可以是令人愤慨地标新立异就像《暴风雨》本有可能变成的样子,要是它把米兰达嫁给了卡利班(Culiban)。与维多利亚时代做个对比就会一目了然。《荒凉山庄》绝不能在一句话话说了一半的时候结尾正如它不能在最后一段里杀光它的主人公们。《米德尔马契》以一个无言的、看破红尘的调子为告终而一名主要的维多利亚小说家是可以体面地趋而避之的,至于《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与《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挑衅性的悲剧终场则仍旧激怒了一伙晚期维多利亚读者群。相比之下,如果斯特林堡(Strindberg)或司各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的一部作品以狂喜的肯定性调子收尾的话我们估计会大吃一惊进而不只一点点地坐立不安的吧。 在哈代(Hardy)之前,有那么一两个暧昧不明的例外譬如《呼啸山庄》,而在英国唯一主要的悲剧小说那就是《克拉丽莎》了。在哈代之后,有那么一些个有争议的例外譬如《尤利西斯》,那是因为喜剧结局在意识形态上严丝合缝。马克思主义者觉察到了这一事实与中产阶级从其进步到非进步阶段的过渡之间的一个关系。然而一个悲剧的反应依然是一个建构性的反应。例如,克拉丽莎之死,可以被视为在她找到了她自己的情境下最适当而机敏的回答。不管怎样,一部作品对它所塑造的情境做出的反应并非简单地寓于它的结论之中。这是一个相关其全程整体对待方式的问题。 人们也不应该将问题与对策模型限制在个别文学文本范围之内。它或许也会在文学模式与文类的水平面上奏效。哀歌和悲剧探究我们如何理解道德,甚至从中摄取一些价值,至于田园诗则冥思苦想我们如何在忠于我们卑微而久经世故的人生之同时又不丧失那珍贵而来之不易的修养。喜剧提出了大量的问题,比如我们的软弱到底有什么如此令人捧腹大笑的。此外现实主义是对关于如何对经验世界的粗鄙保持敬意并看出其中精深端倪的问题的一个反应。自然主义是对文学艺术能否成为一门科学社会学的问题的一个答复。戏剧形式如表现主义者趋向于兴起在艺术家发问如何将现实主义不得不转交给他们的精神或心理现实放在舞台中央之时。像大多数当下的现代主义,它们是对现实主义的问题的“答案”。 文学作品或许不仅仅是针对一个问题甚或还是一整串问题的一个回应。许许多多的光芒被洒在了所谓新约的身上,比方说,当有人将其阅读为对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的解体以及第二圣殿晚期所标志的动荡、希望、分裂、醒悟与焦躁不安的一个多方面反应的时候。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亚》追寻“前文明”复仇的自我延续循环如何被转变成一个文明国家的司法秩序而不用否认那些在更古老的正义体系中可供使用的元素,也不用减轻暴力的施加,或必然为了文明自身的存留而合理化某种敬畏感。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奋争着去调和一种蓬勃的中产阶级有关进步、总体性的信念与带有自由主义对此类雄心勃勃的规划抱审慎态度的宏大叙述,对地方的乡愁与一种人之有限性的悲剧感,一切的一切皆可被看作是一种中产阶级特色,其高度改良主义的愿望受到了大幅度的阻挠。可是所有的这些议论都随之带来了其它问题,转而又要求着其它林林总总的回应。 有一种关系介乎于杰姆逊认为文学作品是联想语境与其反应的见解,与阐释学主张去理解一个文本就是去重新建构相关答案的问题之间。在《真理与方法》中,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承认他在这一观点上受惠于历史学家R.G. 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一位德国哲学家提名一位英国哲学家的一个罕见的事例。10柯林伍德声称每一个命题都能被理解为一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所有此类问题都蕴涵了一个预设。所以“有一只狒狒在我背上”可以被看作是对“用毛茸茸的手臂捆住你喉咙的那个狰狞的、红眼睛的家伙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并且蕴涵了存在着有毛茸茸的手臂而被叫作狒狒的生物的预设。11“你说不清一个预设是什么,”柯林伍德评价道,“除非你知道问题对答案而言意味着什么。”12在一位评论家的口中,一个人需要去问的,在阐释学上来讲,是“某某人(So-and-so)问问题所预设的一个答案是什么?”13了解这一点可以有助于判定预设的正确与否。 柯林伍德相应地想要用一个对话逻辑来置换一个预设逻辑,对他来说其恒定的辩证展开是更合乎于人类所探寻的历史性本质的。于是命题变成了述行行为的内隐实践。它们所反应的是本身或许不复可识、被暂时抑制或搁置了的问题。还存在着柯林伍德所言的“绝对预设”(absolute presuppisitions),既不包含问题亦不包含答案。相反,它们是先验的,因为它们表示了对任何问题的特有辩证逻辑与答案的取得进展的假定都是必要的。根据一位研究柯林伍德的评论家所言:“理解一个给定的问题意味着以涵盖揭示问题未发的不在场的预设来回答之。”14大概也有人会这么来说杰姆逊吧,理解一部文学作品乃是重新建构意识形态语境亦即留存作品是其一个反应的“问题”。 这个阐释模型与文本作为策略的概念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关联的。将一部文学作品领会为一种处理一个隐含问题的途径也便成为了一种本身作为诠释的特殊情况。杰姆逊以提倡思想史是其模型史的说法开始了他对《语言的牢笼》的研究,但他大约还宣扬了它是其问题史的主张。对于阐释学家来说,现实是归还一个负载历史的问题一气呵成的回答。一个承载着可以接受的问题的框架——粗略地讲,路易斯·阿尔都塞命名为问题式(problemic)而米歇尔·福柯称其为一种知识型(episteme)——决定了在一个具体历史语境中什么可以被算作是一个貌似有理或明白易懂的答案。兴许这就是马克思在评价人类只能设定他们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的所思所想。如若我们起初是有意提出一个问题来的,那么一个答案大概也就在不远之处。我们界定一个问题的方式很有可能为我们指向了一种解答,或至少表明了可以算作解答方案一种途径。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里谈论说只有处于能想出一个答案的状态之人才能够聆听到那些问题。 即便如此,产生的问题并不会在它们的尾巴上工工整整地绑着它们的答案。这是因为我们的问号偶尔会收到引人醒目或出乎意料的反应,对不住斯坦利·费什的是,知识中的进步是有可能的。科学因为这一能力才得以兴起,没啥好少见多怪的。在大多前现代思想中,恰恰相反,学习某些事物最主要是为了确证人们早已知道的东西。大部分男男女女所碰到的肯定都是已经熟悉了的,因为,这样说吧,上帝定然不会如此蛮横地考虑不周以至于不曾在太初之际揭示必然使他们获得拯救的一切真理。他要是对古伊特鲁里亚人隐瞒不能犯通奸的重要性而把它写在十七世纪法兰西的天空上的话,那他也未免太不公正太不厚道太不负责任了。 在这一阐释学观念中,并没有什么终极答案,因为答案反过来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远看像一个解决方案近看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唯有在神话里这一过程才能画上句点。当俄狄浦斯回答了斯芬克斯的未解之谜的时候,这只野兽杀死了它自己。然而正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如果提问失败那灾祸也会降临到神话思想之上。佛祖之死归因于阿难(Ananda)未曾求问他活,而高文-帕西法尔(Gawain-Percival)假使没能询问圣杯的本质则会使得鱼王(Fisher King)大难临头。15 如此看来,阐释学批评旨在重构一个问题以阐明一个答案。文学作品反映某些这般循环、自持的结构,那种我们有机会在别的语境下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它们看起来是在自我运作,可是在这么做的时候它们频频将历史材料转换为供给这一自我活动的契机。领会一个文本的意义故而要视其为囊括一个情境的一次尝试——这一尝试在肯尼斯·伯克眼里往往包含了某种征服,也就是某种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象征行为,从神话、魔法、诵经和诅咒到艺术、梦、祈祷和宗教仪式,是人类用意义来统摄外界的一部分方式,就此促使其生根发芽。伯克对弥尔顿《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的评论显示了他那有几分口味高标的风格与另类异质的方法,写作于他就像他所理解的写诗一般“几乎是一类巫术,一位脾气火爆且会在肖像中杀死敌人的老牧师斗士的一通创造奇迹的咒语,他估计是因为采用高度神学[原文如此]措辞来帮助自己进行政治争论而被调任了,然后通过如此这般的放大,他的倚老卖老冥顽不灵简直愈发不可收拾。”16 人类劳动其自身就是一个意义建构模式,一个将现实安排的井井有条以满足我们需求的途径;但为了使它真正高效我们还需要一个元意义建构模式,某个更推测性的形式来反思我们的劳动与语言所开辟的世界。而这,一路从神话和哲学到艺术、宗教、艺术形态,就是象征的领域。如果艺术是我们用心智来统摄世界的方式之一,或更普遍地反思那一过程,并且如果此类意义建构对我们的生存必不可少,那么非实用终究还是归于实用之名下了。不过也有可能其对立面才是正确的——历史地说,实用(或曰必然王国)必然被非实用(或曰自由王国)所超越。这一点,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希望所在。在最值得渴望的未来里我们可以比现在更少地为实际需求所束缚。假使这不只是马克思那边的一个期盼向往,那是因为他相信阶级社会对资源积累的使人意气消沉的实用性叙述最后必将为此目的而切实可得。我们当前辛辛苦苦所生产的财富会被用来将我们从辛辛苦苦之中解放出来。作为策略,艺术作品属于必然王国,或最起码属于被称之为象征的多少不太受到限制的领域。而作为运动,它预示着的是自由国王。 为了说明文本作为策略的思想,让我们简短地一瞥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这首诗在其中追问了为什么清教徒革命分子的凌云壮志会被粉碎——为什么万能的主看起来不再支持他的选民反倒把他们抛弃在了国王与牧师的慈悲之怀当中。这是因为他们的事业被误解了,或是因为他们的无信仰使他们不配旗开得胜,抑或是因为在人性深处的巨大缺陷怂恿着男人去为了不体面的结局而放弃他崇高道德的目的(这个缺陷有时候被认为是女人),又或是因为我主那高深莫测的智慧依然会维护他自己的人民,使他们投入而今艰苦的阵痛其实是他为了最终拯救他们的暗黑而神秘的计划的一部分?伊甸园的堕落回头看来会否是人类存在的一个甚或更宏伟的形式的一段绝对必要的插曲,好比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是社会主义的一段绝对必要的插曲?再或还能否有人可以从这场惨剧中搞出一种辩解开脱——一个为什么 男人和女人追求了失败了,但(如同在古典悲剧理论中那样)并不为此分崩离析负全部责任? 既然弥尔顿的伟大史诗是一首诗而非一本政治手册,它引起这些叙述、情节、戏剧性、修辞、意象、性格、情感姿态等方面的问题并作出反应,这些方面没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抽象性探究表面上的幌子。但是尽管这一背景(mise en scène)将这些议题作为活生生的体验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它同时也复杂化了一整套的文本策略。例如,这首诗以叙事形式浇铸了其神圣的主题,可这样做却也难以自禁地陷入了宗教题材内在的某种窘迫之中而难以自拔,尤其是整个故事看上去都像在讲关于上帝的一件无与伦比的坏事这一点。一旦不朽的真理被投射入世俗的形式之中,一大波道德与审美难题就将不可避免地如期而至。作品的形式,举例来说,不得不在对万能之主的呈现中把他削减到作为一个冷血无情的人物的尺寸上去,正如它努力地去为他对未得救的人民的所作所为做辩护那样。弥尔顿是一名观念上、话语上和理智上的反抗诗人,而他需要聚集所有这些资源去证明一位至高无上者的公正不阿,这位至高无上者会给我们的第一对家长判刑而其罪名则在于吃了一个小苹果。可是这个东拉西扯、争论不休的模式也在冒着破坏史诗效应那纯然的宏伟壮丽的风险。因为弥尔顿的上帝为了合理化他稍许有些臭脾气的行为要做太多太多的争辩了,这首诗走过一个又一个韶华的成功之处在于使这位八面威风而又出类拔萃的造物主听起来像是一位刻板守旧的官僚或罹患便秘的公务员。 还有一些颇成问题不太协调的矛盾介于这首史诗的所示与所说之间。介于,比方说,人文主义的弥尔顿对亚当与夏娃同情的描绘,与这部作品关于这对有罪的夫妻所的采取严厉批判的道德立场之间。这首诗正儿八经的神学性记述间或会与其戏剧性表现不相一致。类似的前后矛盾也可以在撒旦那边找到。威廉·布莱克认为弥尔顿加入了魔鬼的行列而不自知,这并不正确。这名激进的共和国作家所勾画的撒旦是一位妄自尊大的幼主。不过因为他作为一名悲剧角色被再现地如此峻拔伟岸,他窃取上帝权能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作品的意识形态意向。行善似乎引人入胜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时代就变得有一茬没一茬了,而进入现代状态还想继续摊下去则大概是不太可能的。 就像许多文学作品那样,《失乐园》不断地抛出问题而后寻求解决,不时还在此过程中创造更多得多的问题出来。它包括一组策略性的折衷与磋商,其中包括了“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其反对派事实上是引人误入歧途的,因为一部艺术品的形式特征确实和它的内容一样富有意味深长的意识形态;但它会暂且性地难以动摇。在文本不断向前发展的道路上会发生什么则是一个存乎二者之间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复杂问题了。譬如,一个意识形态矛盾,可能临时在一种形式上的变动中被解决;但这一变动可能随即便在意识形态更深层面上滋生了另一个的问题,反过来也便陷入了一个全新的形式困境里,以此类推。 在论及弥尔顿的史诗时研究一下它自身是能够拿来论证这一点的,但我们或许可以简略地来考量一番像《简爱》这般更容易驾驭的一个案例。在结尾处让简与罗切斯特(Rochester)在一起是小说策略性设计的一部分;要是它在一开始没有让他们分开的话,这会违背现实主义的经典准则,更别说在它自己这方面表现了一个太过明目张胆的愿望满足了。这一叙事转向也实现了若干意识形态上的目的。它满足了小说信念(当下受虐的与清教徒式的)对受难与克己的需求,同时防止了它正派得体的女主人公犯重婚之罪。它还让她遇到了作为一种严格律己的他我(alter ego)的圣·约翰·里弗斯(St John Rivers),那诱使她面向了缺陷正如面向了自我克制。此外,离弃不检点的贵族也是小说借以惩罚他对其女主角的德行放肆盘算一种途径。不过罗切斯特被惩处的限度不能过分到他不再发挥作为简欲望的崇高客体(sublime object)的功能。自然啦,叙述势必再度结合这对恋人;但既然手头没有现实主义技巧可供使用,它便被迫去乞灵于寓言手法让简在山长水远之处听见她主人的呼求。 这般冒险助长了是书的意识形态投射只可惜是以其现实主义的减损为代价;但从形式上讲这部作品不管怎样都是惊人而不均匀地混合了现实主义、生平事迹、哥特风格、浪漫传奇、童话故事、道德寓言等等,其效果之一是显示了在人世间一碰就破的表面下寓居着何等不可思议的亲和力与猛兽般奇特的激情。要说这是的饥饿的四十年代(the Hungry Forties)的一个社会文本,那它也是“美女与野兽”的一次再度上演。这部小说因此得以(差不多)侥幸逃脱其反现实主义的战略,而简回到了她苦恼的情人身旁。在此期间,这部作品通过杀死罗切斯特的疯妻来清理了小两口军事联盟的道路,这一举要求了另一次从现实主义本色到传奇剧和哥特式精彩片段的偏向。 既然伯莎·罗切斯特在小说无意识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她丈夫的一个离奇双身(她的肤色就像他那样黑,不相上下的身高、侵越、身为一名危险的异乡客、潜在的毁灭性和充盈的动物激情),毁灭她也就是惩处他的一种取代方式。更准确地讲,它是惩处他而在实际上又不杀死他的一种方式,这恰恰符合了作品为它的女主角所存留的宽厚结局。可是这种道德举措也是一个满足了简的欲望的叙事机制。罗切斯特被惩罚的还有其个人本身正如同其配偶那样,又瞎又瘸,这个故事在他身上发泄了其大规模虐待狂式的、寻找替罪羊的暴怒。这发挥了一个意识形态功能,罗切斯特被迫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代价,而有志于小资的女人则屈尊于掠夺成性的贵族男性。而它也作为一种情节设置发挥着作用,在进行过程中将盛气凌人的显贵削减到相应尺寸并使他人性化或女性化,如此一来卑微的家庭女教师简就可以精神平等地与她的主人永结同心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如愿以偿而又没有阉割掉那个无赖,也再一次地,恰恰地符合了简她自己的利益。实际上,一个受伤的罗切斯特比一个强健的罗切斯特更具有某种魅力。他没那么雄赳赳,也就没那么令人担忧。 不过,简所赚到的比这还要多。罗切斯特的既瞎又瘸第一次允许了她对她的主人行使权力,她牵着这位如今已然颓丧的强健男子的手正如牵着他的鼻子在走。而且,去充当他的同伴,也实现了仆人或温顺而服从的妻子的功能,既否定又保持了简先前的角色。这样的叙事移位因而准许了此书的女主人公取得了她的无意识所寻求的身份与主权,又无损于她的虔敬、端庄与社会从众性,更别提她的性受虐症了。简和罗切斯特的关系到最后同时是顺从、统治与平等的。在夏洛蒂·勃朗特的世界里,再没比这更令人感到满足的了。也难怪D.H. 劳伦斯(D.H. Lawrence)认为这部小说的结尾是“色情描写”(pornographic),它自觉有罪而粗暴地对待它所创造的庄严高贵的野兽男,精雕细刻地将他递交到了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手上。小说的投射如此努力地要去实现的——去达成简她的自我满足,但要安全稳固地控制在社会风俗习惯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总算是实现了。 所以说《简爱》,如同许多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寻找为其历史语境所设立的特定紧迫问题提供的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方案。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谈及文本的“必然性”,又不会被误解为铁的决定论。一个人该如何去调和自我实现与自我屈从、职责与欲望、男子汉气概与女性的顺从、平民大众的精明机警与上流社会人士引人欣羡的教养、浪漫精神的反叛与对社会习俗的尊重、进取的社会野心与对高傲的上层阶级的小资怀疑?17文本策略所致力的这个任务牵扯到一种在“形式”与“内容”的边界间不断跨越的运动,这展示了任何此类分界的终极技法。好比是晨星与昏星,形式与内容也在分析上有所区分而在存在上一模一样。 《简爱》不得不在各种冲突的价值之间做出一个权衡,而在不同的的叙事形式之间也是如此。在试图去走出特定道德或社会的进退维谷之时,它还发现自己被一种好斗的、新近的现实主义与特定传统文学模式缝合在了一起,如雷蒙·威廉斯在对骚动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探求中所展现的对一系列全新社会体验的记录。18当叙事遭遇到了没有任何手头的现实主义方案可以解决的难题之时,无论如何,它有可能会选择重提一个更寓言式或神话式的手法譬如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而这些——适时的遗产、失散多年的亲戚的发现、方便的突然死亡、心灵上奇迹般的改变——在维多利亚小说中遍地可寻。它们在其中指向了现实主义“解决方案”的欠缺。不过这些个笨拙的叙事设置其自身兴许会抛出新的问题,而这一次将轮到它们来“加工”这些问题。 2 这一切的一切看似都已经足够复杂的了;但它在我们察觉到没有一点可以在没有一名读者的情况下得以进行的时候则更有甚之,而阅读也和作品自身一样是一种策略性事业。阅读,于是乎,也就是从事于一套策略以解译另一套。接受理论的成就正在于转向了阅读行为,长时间以为被视为存在视为自然视为睡眠或呼吸,将阅读行为变成一个独立的理论问题;并且这几乎命定了在一个文学现代主义中发生因为彼时文本的模糊性——阅读的茹苦含辛——并不单单是一件偶然之事而是作品意义的中心之一。现代主义文本有为数可观的理由抵制轻松读物:因为它闭关自守,为一位确定实在的读者的不在场所困扰,并将它自己当作它的对象以至于隔绝了任何轻易从外部接近的通道;因为它力求提炼出某些现代存在的破碎与歧义,还有渗透其形式和语言并冒着给它打上晦涩不透明的底色风险的品质;因为它轻蔑地不搭理萦绕它的政治的、商业的、技术的和官僚的话语,它感到那是清澈透明的只不过为此付出了被忽视的代价,还为它自己探索一种更浓厚、微妙与难以捉摸的特色;因为它想要避免被看作一件商品,并运用它的模糊性作为一种防止自己被太轻易地消费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主义艺术的模糊性像极了抵御机制,大自然就考虑周到地以此来配备那些太轻易地受到被一个捕食者所匆匆吃下的威胁的动物们。 詹姆斯·乔伊斯淘气地谈论道他要他的读者花在阅读《芬尼根的守灵夜》的时间和他写的时间一样久,也就是这样的高度现代主义读者,面对着一连串玄妙的能指与对信息的匮乏或过载,促益了接受理论的开端。读者曾拥有的是最低权限,在包含作者与作品的三位一体中乃是最不被重视的一份子,被当成是作者倨傲的特权等级下的一个小小的女仆或杂役,如今终于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作为文学作品共同创造者的身份。消费者转变为合作者。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有一些有趣的评价认为阅读不只是一个“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还是特定习得技能的部署。读者具有特定体验因为她学会了去做特定的事情,精通特定的策略与计谋,如何进入阅读行为。如果她无法调遣这些技能,她就无法获得一个熟练的读者的特有体验。 然而,依凭着接受理论,更多的需求被堆积在了文本倒霉的处理者身上。读者现在有义务去从事于一个将负荷个体最躁狂的精力的策略性事业之中:连接、校正、代码转换、合成、关联、非实用化、图像构建、视角转换、推论、规范化、识别、形成概念、否定、前景化、远景化、反馈、情境化、关键场面构建、整合、记忆改造、期待变更、幻想构建、格式塔完形(gestalt-forming)、图像打破、空白填补、具体化、连贯性构建、结构化与预测。在对着一本书汗流浃背了一两个小时以后,读者所需要的无外乎一个热水澡或一夜睡的香了。 沃尔夫冈·伊瑟尔在《阅读行为》(The Act of Reading)中给出了对这些活动的一个解释,明晰地运用了“策略”一词来形容文本的工作方式。作品的“剧目”(repertoire)由其主旨、叙事内容等等所构成,但这些必须被组织得井井有条,而实现这一功能的任务属于作品的策略。可是,这些策略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文本的结构特征,因为和布置它的材料一样它们创造的条件在于那些材料要成为可传达的。19他们从而得以同时包含“文本的内在结构与理解的行为并藉此在读者那里激起反应”。20它们既作为事实从属于作品,又作为行为从属于作品。 因而,策略组成了作品与读者之间至关重要的纽带,其作为协同活动首先将文学作品带入存在。它们引起了“一系列不同的行动与互动”,21作为展开项目的一部分亦即我们所知的文学作品。文本是一串意义生产的指示,就像一张管弦乐谱。“随着我们的阅读,”伊瑟尔评论道,“我们在幻想的构建与破除之间上下来回地摇摆。在试验与过失的加工之中,我们通过文本对提供给我们的各方数据组织与再组织……我们瞻望,我们回顾,我们决断,我们改变我们的决断,我们形成期待,我们被它们的未完成所震惊,我们质问,我们冥思,我们接受,我们拒斥……剧目的成分通过综合策略性的过度放大、平凡化甚或暗指的消灭而不断地远景化或前景化。”22 在这个潜在而无止境的过程中,我们起初以为解释的假设发现它们自己被其它可能性阅读的逐渐浮现所挑战。不确定性的区域必然被填充进读者的想象、建立的连接、举一反三的推理与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概要中聚集的想象性情境。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考虑我们原本以为不成问题的详情,故而也重新调整了我们的先入之见。文本的接受者必须介入去填补语义间隙,从大批的可能性中选择她自身觉得更可取的解释道路并检验差异,或许是矛盾对立的视角。作品可以在进展之时系统论述其本身的规范与惯例,而在此计划中读者乃是一名十足的参与者,倘使不算是一名合著者的话。作品的所有权,可以说,仍旧归于作者——但这是一名具有积极社会良知能够关怀他人的、思想自由的作者/雇主,会许可与他们关系有所不对称的读者/雇员在可以和睦共处的情况下对此事业的运营得以言其所欲言。在这一见解下的文本的意义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实践。它在作品与读者持续的往来之间呈现而出,所以(以拉康式特色来提及这一事由)阅读行为是一个人从另一个(文本)改观或梳理的形式中获得自己的反应的事情。 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杰姆逊的自我塑造的迹象。“随着我们的阅读,”伊瑟尔评价道,“我们对我们自己所生产之物做出反应,也正是这个反应模式,事实上,使得我们能够将文本体验为一次实际事件。”23一部文学作品应当被理解为“对它所选择并吸收在其本身剧目之中的思想体系的一个反应”,一个惊人地接近于杰姆逊本人的阐述。24与大多数接受理论家相同,伊瑟尔显露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识的欠缺,或实际上是对除了文学历史之外的大量历史的意识的欠缺;不过伊瑟尔式作品对其所产生的一种我们已经检验过的案例的反应的方法则并不难看到。其实,伊瑟尔一度以明晰的杰姆逊式术语来阐述这个问题,说什么他需要文学作品“去包含它所反应的完整的历史情况”。25 同样地,斯坦利·费什也把阅读当作一套策略来对待,但如同一个攻无不克的将军的战役它在其路径上摧毁一切并且不遇到任何阻碍。这是因为并不存在着什么阻碍它。“在这样一个[接受理论]解释中的每一个要素”费什坚持认为,“确定性或文本片段,不确定性或间隙……皆会成为一套需要它们的解释策略的产品,因此那些要素中无一能够独立地作为解释过程的依据而被赋予。”26解释从而就像它所讨论的虚构作品那样,是自我生成并自我合法化的。既然它生产的亦即它意在研究的,那所有的解释就都是自我解释了。你在显微镜下所瞥见的微光原来是你自己的眼镜。 大抵上说来,区分看待文学作品的两种方式是有可能的:作为对象与作为事件。27前者的一个范例是美国新批评,对其而言文学文本是一个仔细分析符号的封闭系统。它是一座大厦或一个具有建筑特征的结构,连同各式各样的层面与子系统,那被期望为存在于读者头脑中的一个共时整体,而非一个有着其本身历史演变的戏剧或象征行为。诗歌在新批评派看来具有一个瓮或塑像的宝石般硬度,挣脱了作者意向的牢笼,自成目的而不可改写。 颇为反讽的是,文学作品可以说正是在其抗拒商品形式的行为中模仿了商品形式。它感觉上的质地是对商品抽象概念的一种非难,它剥去了它肉体存在的世界。然而作为一个自我闭合的对象,废除了其本身的历史而且没有明显支撑的手段,作品本来便成为了物化的一个实例。作为竞争力的一种微妙平衡,诗歌担当了自私自利、片面性教条还有过度专业化的一种无言的批评。同样地,它对同时代的社会秩序作出了一个含蓄的评论。然而他至高的平衡力有一种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样子,这反映了一个技术时代的科学主义。它还反映了对党派性的一种自由派的敌意。诗歌也许可以剥离历史,也就此剥离意识形态;但如果意识形态被视为现实矛盾的一种想象性解决,那么文学文本便恰恰成为了它以偏见的目光所投向的现象的一个模型。 俄国形式主义是另一个把作品当作一个客体对象来看待的例子,尽管在时间的长河中它超越了尤为静态地视其为一个“技巧的集合物”的看法而转化为一个对其运作更协调的、动态的概念。28布拉格结构主义者从俄国那帮同胞之处接手了这一文本理论,视其为一个功能系统与一个总体结构。然而一个策略远不只是一个动态组织的事情而已。毋宁是一个具有特定内置意向性的结构,为了达成特定的效果而组织起来。它是一项工程,而非仅仅的一个系统。它的内在配置取决于与它所处理之物的积极关系。就形式主义者而论,这是“去自动化”读者认知的过程。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诗歌的内在复杂性为一个“外在”目的而存在,也就是说这里生效着一个从作为对象的文本到作为策略性行为的文本的试验性的过渡。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将文学作品写成是“一个复合、多维结构,由审美意图的统一合并而成”。29值得注意的是“设计”(design)一词同时意味着它旨在实现的一个结构与一个意图。 就此情形而言,形式主义者作品作为对象的概念略微与疏离的观念有所不和。疏离,无疑,可以被明确为文本给定特征的术语,在这个意义上也就属于它的客观结构。但它也是一个事件。是语言在对读者做一些事情,也可以说是修辞。而那则相当不容易被明确,它所取决的远甚于文本自身的外形。形式主义者的工作相应地悬浮在对象与事件之间,接着按下了抉择前者的按键;而这主要是因为诗歌的策略性目的——认知的改观——对它来讲是如此彻底的内在固有。即使这样,使其陌生的加工过程也包括了对读者的一种改造作用,意即诗歌同时是审美系统与道德实践。 文本作为策略的观念在形式主义者的散文体小说观上则显得更为分明了些。这些批评家习惯在文学叙事中区分“故事”(story)与“情节”(plot)——前者指的是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而它们可以在叙事中被重建,后者的意思是作品自身对这些事件的具体而独特的组织安排。因而,情节可以被看作是对故事材料的一个策略性操作,以一种赋予它们全新可感知的底色的方式(通过悬搁、“制动”(barking)、“延迟”(retardation)等诸如此类)重新组织安排它们。 那么,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就对象/事件而言的特性的关联又如何呢?存在着一系列的符号学将文本当作分析的对象来看待,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与米歇尔·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的著作就是如此。30但也有其他的符号学潮流——例如,翁贝托·艾柯的著作——那更接近于我们所见的接受理论,对其而言符号的诠释是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实践。31艾柯所谓的“符号生产”(sign-production)是读者部分的一个活动,他们凭借外展(假设)、归纳、演绎、超符码化、不足解码(undercoding)和其它此类策略,解译在文本中是“一个可被给予多样理解的空白形式”的“信息”。32文本比一个允许我们纵横交错地穿来穿去的”小径分叉的大花园”具有一个更不稳固的结构。故而相比跨越威斯敏斯特桥来讲阅读倒更像是漫步在海德公园。这些穿插在艺术品中的通道或“推论路线”包括了读者时而认可时而驳斥作者的代码,时而不解“发送者”的规则是什么,试图从数据分离的片断中推断此类解释方针,提出她本身特定的试验性代码以理解作品成问题的段落,如此等等。文本“信息”不仅仅从代码中被读取;它们是对产生它们的代码而言不可化约的事件或符号行为。这令人想起维特根斯坦对规则应用的创造性本质的论述。如查尔斯·阿尔铁里所言,施为句不能被简化为言语建构。33并且既然代码自身或许会被读者的生产行为所改造或改观,它们可以继续提出截然不同于那些它们已然生产的意义。 文本的符号于艾柯看来并非稳定构件而是编码规则的短暂结果;而代码自身并非固定结构而是读者安放来说明一个“信息”的临时手段或可行假设。就其本身而论,它们只在履行阅读之时才会被构成,暂时把文本的部件拉在一起以显明其意义建构的模式。文本的信息不是一个单方前提,而是允许读者方面“多产推论”的一个“约束网络”,就像是富有生产性的“偏离”那样。相比对此类意义生产的一组有时几乎难以辨认的指示而言一部作品更非意义的一套指令;这甚至适用于其个体符号,比容纳了各种各样的语义可能性的“微缩文本”(microtexts)更不是索绪尔的离散、自我同一的构件。在符号与文本共同的层级上,符号过程(semiosis)终究遁入了无穷。生产与符号的接受,还有文本与信息全都是迷宫般错综复杂的投射。而且既然这一符号活动在原则上是无限的,如同一个符号的意义只能被另一个符号来配备并依次轮流交替下去,那么对于陷入苦网之中的读者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原来的栖身之处。我们在对付的并非一个稳定的结构而是一个结构化过程。正如艾柯所说:“审美文本不断的将其外延转化为新的内涵,其部件无一停留于它们的初始解释项(interpretant),内容从不为它们自身缘故被接受而是作为其他东西的符号载体”。34 在此过程中,作品的每个特征都被读者所实存化(actualised)了,接着作为一个结论而推动她进入全新的诠释活动当中。人们应用临时特定的作品代码来实际化一个文本的结构,与此同时对作品在如此结构下的投射做出反应。这一点,人们大概会认为,是艾柯自身符号学版本的杰姆逊式模型。读者与文本的相互作用,读者在其间对她发现自己所反应的特定意义进行投射,相当于杰姆逊的文本与潜文本的往来观。艾柯的文本作品同时是结构与事件,事实与行为,且彼此间互为依据。文本的代码与读者的代码无休止地互相渗透。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对照于被称为书籍的物质客体对象,是不具有一名读者的“实存化”的,但这个活动并不是自我决定的。尽管被文本它们自身的结构所规定是绝不可能的,但它还是被它们所暗示、引导与约束。(这一点,人们可能会注意到,是艾柯的方法与一种斯坦利·费什厚颜无耻的哲学唯心主义之间关键的不同之处。)在解码文本之时,读者于其上享有特定最高权限;但这个管制的资格是以一种独特而明显的方式实现在实际的阅读行动之中的,这到了权限与行动变得难以辨别的程度。读者并不单纯具备了一种她随即便可以顺心地实现的固定能力,就像在温布尔登网球场的一名网球运动员没法通过在更衣室里硬着头皮开始学这个游戏的技能,随即便上场并将其付诸实践而后就能取得冠军一样。 正如存在着多多少少符号学的策略性形式,与此相当的特性也适用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者]名目下的[一部作品的]要素,”沃尔夫冈·伊瑟尔写道,“产生了一个秩序,其技巧的总括将一个又一个要素联系在了一起,故而呈现出了组成文本最终结果的一个语义维度——不过所有这些都没有阐明到底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呈现出来,它如何发挥功能,又是谁在使用它。”为了应答这一稀奇古怪的枯燥难题,伊瑟尔以维特根斯坦式的语气引用了一位德国同事的俏皮话讲道:“一个人只有在理解的不只是语言之后才能够理解语言。”35只有通过把握这个文本结构的功能——也就是说,把握其与一个语境还有视其为行动的关联——结构自身才能被适宜地揭示。就此意义上来说,文本的结构不是最终的已知事实。这还是普遍适用的,一个结构只有在它是可明确论证或自我诠释的时候才可以成为基础。只要它需要被诠释,就有某物优先于它,即语言在这一诠释发生之处。36 “文学文本的结构,”伊瑟尔写道,“只有通过文本的功能才会有所相关”,37这个主张等同于提议文本最好被视为一套策略。一套策略正好就是一个大致上由自己的目的所决定的结构。事实上,伊瑟尔的主张不但符合于文学作品,还符合于意义本身。意义,毫无疑问,在一定层面上是一件结构的事情,结构主义者是急于要坚持这一点的;但符号之间体系的差异是言之有理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我不知道在仅仅知道“现实”和“诚实”不是一个意思的情况下如何知道“诚实”这个词的用法,其实在特定意义上它恰恰就代表了前者的反义词。相反我需要把握它在一个给定生活形式中功能。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部文学作品的功能是一件极度变化无常之事。作品,如我们所见,有可能达成所有范围的目标,从激励年轻战士血战沙场到乘以四倍某人的银行存款。不过我们还看到了文学文本也有一种内在语境,其中有一种内在关联;在这里,一般来说,也是功能决定了结构。是作品试着就其语境所做之事决定了它挑选的手段与演进的方式。伊瑟尔评述得很是到位:“如若文学文本表现了导向一个给定世界的一个意向性行为,那么它所着手的世界就不会仅仅在文本中被复制;它会经受多方面调整与改正……在梳理文本与超文本现实的关系中,[功能的概念]也会梳理文本所寻求解决的问题。”38“多方面调整与改正”这般谨小慎微的官腔很难公正地处理世界进入文本的强有力的改造过程;不过伊瑟尔正确地讲功能的概念与作品的观念视为紧密关联的问题来解决。 有一种结构主义打算借助文本联合它们离散的要素成为意义的统一体来确定规则,这是文本作为对象的一个老生常谈。热拉尔·热奈特与A.J. 格雷马斯(A.J. Greimas)的叙事学大可于此引以为例。39还有人认为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文学分类法亦是如此,他不怎么算一个结构主义者不过偶尔看上去像是一心一意地觉得分类活动的本身即为目的。雅克·德里达曾经将这种分析批评为要生机勃勃也“只有在力学上,永远都不会在能量学上”。40最令人心灰意冷的是,它未能将一部文学作品领会为一段修辞——也就是说,领会为尝试去做某事。这是来自佐格星球的文学观。然而也存在着一类结构主义颇志同道合于我所倡导的文学见解。其中一个证据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意见:“神话思维从对对立面的意识向对它们的解决前进。”41“神话的目标”,他写道,“是提供能够克服一个矛盾的一种逻辑模型。”42由此看来,神话是“善于思考的”策略,是处理自相矛盾与相互矛盾的前现代机制。人们不需要全心全意地赞成这个神话学理论也可以觉察到其对文学分析的价值所在。 至于伊瑟尔的接受理论或艾柯的符号学,神话并不一下子而是作为一个策略性过程完成这一任务,如同一组对比被转变成另一组接着再是第三组,一种矛盾被调解为对第二种矛盾的开启,一个要素被另一个也要被取代的要素所依次取代等等。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无休止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正发挥着作用,一个神话学文本吞食另一个而后再被第三个所交替上场。一个神话的无意识意义,列维-斯特劳斯论述道,是它所寻求解决的问题;而为了成功解决它将此类意识机制展开为意象、情节和叙事。但是,我们被告诫不要把意识与无意识、情节与问题当作镜像或同源,而要当作一种转化。基本上和杰姆逊模型里的文本策略及其潜文本的关系差不多。 神话对列维-斯特劳斯而言是一种“具体科学”,预示了后来的具体科学会在启蒙运动中作为审美而出现。43在一定意义上,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它们只有关于它们自己,就如同象征形式中人类心智的结构被发现在纠缠于其本身深奥难解的运作方式。在这层意义上,它们是某种前现代版本的象征派诗歌或(后)现代主义小说。诚然神话在看似描述现实的行为中揭示了这些心灵运作方式;但在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看来,他们所意在描述的世界也是他们所建构的世界。虽然如此,借助于以一个仿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锱铢必较的精确度来分类那个世界,它们让男男女女更感觉在家般轻松自在,从而也改进了它们的实践功能。它们是认知映射的形式,就像是理论反思或审美举动例证。在所有这些种类中,神话在结构主义者来看与文学虚构之间存在着有目共睹的相似性。 这般见解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如下段落中展现了出来,我自己又在括号中穿插了可供替代的阅读文字: 萨满神话和不和一个客观现实相一致是[作者的虚构也没有一个直接的指称对象]无所谓的。病妇[读者]信仰神话[虚构]并且从属于一个信仰它的社会[文学机构]。保护神与恶灵,超自然怪物与魔法动物,都是关于宇宙建立[意识形态]的自然概念的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的一部分。病妇[读者]接受这些神秘生物[悬搁她的疑惑],或更确切地讲,她从未质疑它们的存在。她所不接受的是成为她系统中的一个异己元素的支离破碎而又任意妄为的痛苦[社会压迫与矛盾],但萨满[作者]却号召神话[虚构]来重新统一俾使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一旦病妇[读者]理解之后,她所做的就不止于听从她自己;她更是恢复了健康[重返了她在社会生活内的实际角色当中]。44 无疑这种神话与虚构之间的相似性看起来略显简化了。不是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会产生这样一种作为生硬的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事实上,大量“经典”文学作品都与它们时代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格格不入,正如大量流行或非经典作品会俯首帖耳地去复制它。人们不应该犯糊涂而将经典与守旧以及流行与进步一视同仁。即便如此,还可以说存在着某些上述讨论的不完善的变调。从这个角度看,神话不该只被考虑为一个机器,它更是一个象征行为。它是一组弄清问题与矛盾的技巧,要不然就没辙了。 西蒙·克拉克(Simon Clarke)认为鉴于早期列维-斯特劳斯把神话当作解决问题的手法来对待,他的后期著作以更理性的精神把它们看待为无所偏袒的心智活动。45如今,在它们的实践动机被褫夺了以后,它们单纯地就是依据平行、对照、逆转、同源等诸如此类的一个逻辑来组织世界的方法,而这几乎过分拘泥小节的布置并不迫切需要任何超越它自身的正当辩护。有人或许会以阿尔都塞式的口吻主张神话在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中相应地从意识形态转移到理论——从正当化通过提供对其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方案的社会秩序,转移到纯粹认知形式。 可是此类认知,就其满足对秩序的狂热来讲,在意识形态上并不怎么比阿尔都塞的理论概念来得更加无关。克拉克谈及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Mythologies)在实践一种纯然内在的分析形式,神话是心灵普遍法则编码后的表达,并不对它们自身做任何外部处理。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列维-斯特劳斯研究神话的方法不只从意识形态转移到了理论,还从现实主义转移到了现代主义。类似于某些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本,神话是自我指涉的。实际上,把结构主义自身看作是对高度法国式的理性主义与一个同样高卢式的象征主义世系之间一个不相称的结合是有可能的。理性主义在普遍心理结构的观念中是在场的;象征主义依凭的事实是这些结构在根本上只相关于它们自己。相反,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中更“现实主义”或实用性的动向,在于将神话看成是对大自然与社会的策略性操作,是设定、调和与改变对立状态的启发式虚构。这样做时,它们寻求解决此类谜题诸如人类如何同时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并能够分离出来,或男人和女人如何同时诞生于大地之上与人类父母之间。 照此,这些部落传说采用具体手段去对付抽象问题,这也是它们与文学作品相像的另一个地方。我们于此所谈及的神话制造者像一种手工艺人一样心灵手巧,这名手工艺人为了完成任何他有所打算的象征任务而拼凑起了任何他在手边能够找到的碎片与残渣(事件的残余物、可循环的象征、其他神话的断简残篇等等)。(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弗洛伊德无意识观念的一种见解,那无意识必然可相比拟地胡拼乱凑各家现成的零零碎碎以装配成被称为梦的文本。)与之相比,《神话学》中的神话制造者总的看来是一个更重理智、讲审美的生物,他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读后感(五):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第四章:虚构的本质 1 有关虚构的理论大概是文学哲学中最为复杂艰涩的方面了,并且还是最经久不衰地吸引了学术关注的理论。因为某些稀奇古怪的缘故,对这一主题的说明不仅产生了一些真知灼见而且还产生了远远超乎大家公平分摊的令人不爽的陈词滥调。例如,格雷戈里·柯里向我们讲述“当一段推论具有相对较高程度的合理性的时候我们说它是合理的,当一段推论具有很低程度的合理性的时候则说它是不合理的”。1彼得·拉马克以“虚构人物,像沃尔华绥(Allworthy)先生或布丽姬特(Bridget)小姐,并不作为真人存在于现实世界”2的事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主张“被虚构的就是被编造的”,这一命题我们稍后就拿来质疑质疑。3一名作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并没有被逼着去宣称一个诸如‘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住在贝克街’之类的虚构的声明必须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即便是针对分别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自个儿与贝克街自个儿,也是一个道理”4。玛格丽特·麦克唐纳(Margaret Macdonald)火急火燎地传播着“简·奥斯汀的小说真实存在”5的新闻。拉马克和奥尔森写道“人类对文学所拥有的兴趣,在于它具备一个人所感兴趣的内容,在于文学呈现的与所说的的东西像人类一样使读者关心”。6“虚构”,格兰特·欧文顿揭露道,“使用的乃是词语,而其绝大部分原因在于丧失了表情、声音和动作的辅助。”7“普鲁斯特,”我们从格雷戈里·柯里这里学习到,“要是不用词语的话就几乎无法传达《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全部微妙之处。”8 然而,这番陈词滥调,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被稀奇古怪所弥补的。关于虚构的哲学充满了和蔼可亲的悖论与谜题。克利斯朵夫·纽追问冥王星是否地真实存在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里,即便它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发现。9他又询问奥菲利亚(Ophelia)是否拥有确定量的或不确定量的牙齿,而在《伊利亚特》(Iliad)的世界里青霉素在二十世纪是否真的会被发明。彼得·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为此论题而辩护说虚构的创造物是有的,而且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着。10 异口同声的还有R. 豪厄尔(R. Howell),他彻头彻尾地信服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存在。11A.P. 马蒂尼奇(A.P. Martinich)和阿弗拉姆·斯特罗(Avrum Stroll)更胜一筹地论辩道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创造物。12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在一篇经典论文里,全心全意地赞同了他们。13托马斯·帕威尔(Thomas Pavel)宣称虚构人物是不存在的存在者。14大多数文学哲学家相信夏洛克·福尔摩斯有一个大脑和一个肝脏尽管故事里并没有提及这些器官,但关于他背后是否有一块胎记的问题则尚有很大的讨论余地。大卫·诺威兹相信在进取号星舰(starship Enterprise)[1]上真的没有一块防热罩。他还觉得匹克威克(Pickwick)先生是真实的,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萨姆·威勒(Sam Weller)[2]可以看见他。15对于哲学家亚历克修斯·迈农(Alexius Meinong)来说,一个正方形的圆是一个客观对象,尽管不是一个存在者,而对一些文学哲学家来说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也是如此。16一个人对一部小说的回应兴许还能有助于判定一个人的国籍。检测想要成为大不列颠公民的外国人的问题之一是“圣诞老人住在哪里?”这是佐证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的主张的一个案例,亦即非存在的实体可能会对世界上存在的实体产生真正的影响。17 约瑟夫·马戈利斯(Joseph Margolis)断言“在一部小说里没有一个句子是能够符合于一个真正的人的”。18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雷蒙·威廉斯就没有必要正好在一名真正的工党议员假装淹死的时候放弃去写一名工党议员假装淹死的小说了。他应该把这部虚构作品继续写下去才对。格雷戈里·柯里相信“两部作品在言辞结构上相似是有可能的——连拼写的细节与词语的规则都一直相似——但其中一部是虚构的而另一部则并如此”。19戴维·刘易斯谈到可能会有一个阿瑟·柯南·道尔所不认识的人,那人的冒险碰巧完美无缺地与他的英雄相吻合,甚至还取名为夏洛克·福尔摩斯,但这个故事并不是讲他的。20肯达尔·沃尔顿(Kendall Walton)坚持认为当我们在观看一部恐怖片而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只是“虚构地”,而不是真正地,感到恐惧。21他还觉得我们无法对不存在的人具有真实的感受,最多只能有虚构的感受。22“在某些[关于叙事的]情况下,”他告诉我们,“那是虚构的尽管叙述者非虚构地去描述或写作,而在另一些情况下那是虚构的因为他的立意就是虚构。”23这些评论中的绝大部分,读者会注意到,揭开了关于文学哲学家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真相。那就是他们关于文学作品的全部知识看起来都是由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所组成的,顺带还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第一个句子[3]。24 虚构与文学并不是同义词,虽然乔纳森·卡勒宣扬什么“把一个文本当作文学来读就是把它当作虚构来读”,而莫尔斯·帕克翰(Morse Peckham)的意见以为使得一部著作成为文学的是它的虚构维度。25包斯威尔(Boswell)的《约翰逊传》(Life of Johnson)与哈兹里特的《时代精神》(Spirit of the Age)通常被列为文学,但既不是虚构的,又不总是被当作虚构来读的。还有大量其他被归类为文学的著作亦然,从西塞罗(Cicero)的演说和塔西佗(Tacitus)的罗马史到培根的《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的箴言、莱辛(Lessing)论戏剧的作品、柯贝特(Cobbett)的《乡村羁旅》(Rural Rides)和艾默生(Emerson)与麦考利(Macaulay)的散文。我们不需要为了把它们当作文学而非得虚构地去阅读它们。文学不限于虚构,虚构也不限于文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记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有一些人确定无疑地将其视为肆无忌惮的虚构,他写道“作为政治修辞[它]几乎拥有着一种圣经式的魄力。总之,根本就无从否认它那作为文学的超强力量。”26 “一部作品到底是不是文学”,约翰·塞尔写道,“是由读者来决定的,而它是不是虚构则由作者来决定。”27正如许许多多的格言警句一般,其正确性乃是模棱两可的。需要不只一名读者来确定某个文本是文学(塞尔显然将这个词限定为价值判断的问题),而一种“虚构化”的阅读则有可能会撤销一名作者的非虚构性意向。塞尔以为一个文本是否为一部虚构作品的准则存在于它的作者的意向中。门罗·比尔兹利同样也主张艺术的概念是有起源的,包含了对艺术家有意想做的或她以为在做的事物的特定参照。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与马丁·施泰因曼(Martin Steinmann)坚持认为“一段话语是虚构的因为说它或写它的人想要它是虚构的”。28但如果我想要在一种特定的情境里以一种特定的模式写一种特定的主题,我大约会被当成在写虚构而不论我想的到底是什么。就算在扉页题写“一个真实的记述”也仍旧无力回天。对于一个人被外星人劫持的耸人听闻的记述将运用到所有熟悉的科幻小说的手法并且在书店里很容易被当作虚构作品而被放在了亚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旁边,尽管此人是在一艘加速驶向另一个星系的宇宙飞船里写下这部小说的。 相反,我也有可能认定我的讲述是虚构的以使其被当作普遍的事实来为人们所接受。作者的意向不会简单地决定读者的体会。就像一种“虚构化”的阅读可以颠覆一名作者的意向从而生产出非虚构,所以一名读者也许会把被意在虚构的一部作品看作是非虚构的。有过一个案例说十八世纪有一名主教将《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svels)掷入火中并愤愤不平地叫嚷道他对它一句话都不信。因为相信一个意在真实而实为虚构的文本不应是虚构的,这名主教被罢免了。斯坦因·豪贡·奥尔森正确地看到作者的意向是由他们自身的社会规范所决定的,这符合的远远不仅是虚构而已。29一名小女孩不可能想要变成一位脑科医生假如她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对于女孩的观念是她们除了成为家庭主妇以外的任何想法都是绝对难以置信的。我们对其怀有欲望、后悔、羞耻、幻想等感觉的对象是由我们社会存在的形式为我们所量身定做的。 有人或许会认为将一个虚构的文本当作真实的来看待并不会改变它虚构的事实,而且这也肯定是作者所考虑过的想法。将一个真实的文本当作虚构的道理也一样。但虽然约翰福音的作者无疑想要他的著作成为真实的,许多人在今天却会将它排在虚构之列。这些人大概也会辩解道他们关于这个争论的判断是胜过作者的。至少在大多数时候,一个作家知道,他所写的是真实的还是编造的,但这只有在严格专业的意义上才能解决它是虚构与否的纠纷。那些在此求助于作者意向的人普遍地被一个太狭隘的虚构性观念所折磨。我们可能会以作者的一个词来抉择他的作品是否是真实的;但纵然他宣布了它是真实的,他实际上也不能指示我们不要去将其视为伪装的借口,或从中寻求某些典范性的内涵,或非实用性地去对待它,上述的林林总总都是我们称之为虚构的方方面面。他更不能阻止我们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它的语言、叙事结构等类似问题,还有依据它的形式来探讨它的内容,或者完全地为了后者而忽视前者。 在这一层面上,诉诸其作者的意向以确认作品的虚构或非虚构身份是彻底过度地简化了虚构性的含义的。不管怎样,一个原始的意向都有可能被无涯的时间所逐出家门。我或许想要用我可悲可叹的素描来表现一只大象,可它却看起来像是穿了一双长筒丝袜的爱丁堡公爵以至于现在每个人提起它来都这样说,包括我自己。弗兰克·迈考特(Frank McCourt)可没有想要《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成为一部小说,但是经过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如此地加以对待之后,再去阻挠它的虚构之名就会显得又乖张而又迂腐了。这并不意味着它所记录的事情没有真正的发生过。这部著作同时既是小说又是传记。 奥尔森议论道“不需要什么慧眼独具也能够识别出‘虚构’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过这是因为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具有价值的术语,而虚构(如流行文类)则未被赋予这种荣誉。30他坚信所有的文学都是虚构的,而反之则不然。确实并非所有的虚构都是文学如果那也涵盖了,譬如,玩笑在虚构的范畴里。不过更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坚信并非所有的虚构都是文学因为一个人不应该把流行小说归类到里面。而所有文学也并非都是虚构,我们刚才已经观察过了。一位评论家注意到存在着广泛的意见认为“虚构性是文学定义必要的(尽管不是充分的)特征”,31但其实,如其他我们所检验过的“家族相似”的特征一样,它并非如此。 卡勒觉得虚构主要在于“讲故事”,32可是非叙述文学形式诸如抒情诗或哀歌也是虚构的,尤其在它们为伪装提供材料的意义上来讲。约瑟夫·马戈利斯认为没有人能够恰当地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济慈的颂歌为虚构,但为什么不能够则很难看出来。33虚构是一种本体论范畴,而非首先是一种文学文类。一首诚挚热烈的抒情诗与《洛丽塔》(Lolita)是同样虚构的。虚构是一个关于文本如何表现的问题,还是关于我们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而首先无关乎文类,当然也无关乎(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它们是真是假。不过也不存在什么好理由去限制这个术语在记叙文中的运用,正如一些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只是在十八世纪虚构变得与小说更同义或更不同义了。把这个术语限定在记叙文里仅仅代表了你更倾向于去忽视诗歌与戏剧中的一些相关因素罢了,还有在这些形式中的一些意义重大的密切关系也是如此。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甚至建议用“叙事”这个术语来替代“虚构”,不过实在看不出来这有什么用。34这样做忽略了非虚构叙事的存在,当然还有非叙事虚构呢。 本尼森·格雷,照常采用了一般人的看法,告诉我们“一种虚构指的是关于一个编造的事件的一份陈述。也就是一个被创造或捏造而非真实发生的事件”。35可是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可不像说说的那样稳固,而且一旦回首从前便会愈加模糊不清。西塞罗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还是艺术家,昆体良(Quintilian)则视史学为一种类型的散文诗。伊索克拉底(Issocrates)和他的一些古希腊同事们把历史书写看作是修辞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史学可以囊括神话、传说、爱国热枕、道德熏陶、政治证成与一点点文体风格上的精湛技巧(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李维(Livy)、塔西佗)。这一事实罕有什么问题可言。 大部分研究虚构的哲学家而今都持有下述观点,这至少同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一样古老,即虚构命题既非真亦非假因为它们本来就无意于真正的断言。就如同康德的审美判断,或相当多的意识形态立场,它们具备真实报道世界的形式,但这是迷惑人心的。而真相则是它们修辞性地发挥功能,在描绘事物本来面目的装束下表现价值与态度。当然,并不是说,非虚构总是断定的反之虚构则从不断定。虚构作品在很多时候都会提出真命题,比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有一场世界大战肆虐的事实,而非虚构文本像安全通告就有可能由警告与命令所组成。充斥着非断言式的言语行为的考卷还被以为是问题而已。只有我们日常言语的一小部分是着重于描绘事物本来面目的。玩笑也许会利用真实的陈述并把它们的真实价值临时悬搁起来。陈述的状态会随着它们从“语言”转化为“话语”而改变——从关于世界的一般命题到在于交流的特定言说或行为。一部小说中或许被视为非真非假(因为没有意在断言)的一段陈述有可能会因为在一个酒吧里被人说出来而成为或真或假。也有可能现在不真实的一个断言过后便成了真实。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所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那个时候不是真实的,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日子里成为了真实。这份文件比刻画它自己本身更好地刻画了我们时代的特性。36 无论如何,搁置一部作品的真实价值的问题不会自发地就将其转化为虚构。你可以简单地不在乎一部广告声明的真实与否,而不必要地说你就是以虚构来对待它了。你可以不把它当作使人信以为真的借口,或在任何其他的方式上我们也可以“虚构化”一个文本。反之,你不需要忽视虚构陈述的真真假假,即使扉页上的名词“小说”邀请你这么做。你始终可以注意于作者对纯麦芽威士忌制造的记述是如何滑稽可笑地谬之千里。而这一点,我们稍后将会看到,它是如何间或地损毁了虚构的效果的。你还可以高度重视一个文本因为它的世界观作为深邃的事实震撼了你,而你全然可以不管不顾地意识到组成那个观念的经验性陈述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令人半信半疑的,要么就是无关乎对错问题的。 尼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特立独行地出没于艺术哲学家行列,主张“一切虚构都是字面上的文学谎言”,但也可能会是“隐喻”真实。37伯特兰·罗素的观点也大致相同。格雷戈里·柯里则近似于柏拉图而坚持虚构作品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虚假。他执此见解因为他认为真实与虚假是关于含义而非力量的问题,故而一个虚构文本的非断言性力量并不能将虚构命题从此类判断中悬隔起来。38他还认为我们是在“倾向性,而非偶发的意义上,不信任一个虚构的命题的”,39意即在阅读之时我们不会在头脑中惟妙惟肖地形成它们错误的点点滴滴,只是当我们被问起之时我们会公认地宣布我们不相信它们。这一点,类似于柯勒律治的“终止怀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表明了阅读虚构行为的阈限本质,在圈套与现实之间的某一处戛然而止。我们随后再来看一个相似的两义性矛盾心理,一个关于如何可能同时去做某事并假装去做某事的观点。其实小孩子们如此轻易地在使人信以为真的游戏中窜出窜进就暗示了事实与幻想之间存在秋毫之末的某种未知的领域。这并不怎么令人感到意外,若是考虑到精神分析学认为好些我们所言的现实原本就是幻想的话。 一部作品就算在每字每句上都是真实的也仍旧有可能是虚构的。柯里接受了这个看法,但只有在相当没有效力的合理性中一部历史小说才有可能以其创造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并在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虚构在他看来只会是“一不小心”真实的,即在一个编造的叙事恰巧与一个作者一无所知的现实进展的事件不谋而合的时候。如柯里所见,不久前在《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上曾刊登了一个故事提到说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只有六个星期好活了,而这最后演变为了几乎分毫不差的真实。尽管读者们并不相信《询问报》所说的是真实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当然不会相信,他们在其他事物中阅读它们因为他们愿意去信以为真。 然而,在一个文本更微妙的层面上可以同时存在着真实与虚构。雪莱在《为诗一辩》讲过一句令人难以忘怀的话:“想象那些我们所知道的”。去信以为真某些你知道是真实的东西并不在实质上不同于信以为真某些你意识到是虚假的东西。一个作家会“虚构化”一个事实上为真的记述,以戏剧化的形式浇铸它,塑造使人无法忘却的人物形象,把它具体化为一个引人入胜的叙事并且组织它的特征来强调特定的道德主题与中心思想。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或可引以为例。《安琪拉的灰烬》亦然。你读这本书也许不是为了它所记述的经验真假而恰恰是奔着这些“文学”品质而去的。 你也许还会对一部立意纯然在于事实或实用的作品采取一种虚构的立场。非实用性地对待一部实用性的作品是有可能的,通过(譬如)在作品之中寻求某些典范性的意义来使它“再功能化”并以此将其从它的意向功能里分离出来。你也可以实用性地阅读一部非实用性的作品,就像历史学家们在《麦克白》(Macbeth)中搜查十七世纪早期关于巫术概念的信息。彼得·麦考密克(Peter McCormick)认为那些邀约一种虚构性阅读的作品总是被如此标记的,但你也可以去虚构性地阅读密尔的《自传》(Autobiography)甚至于《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Species)尽管显而易见的是此类作品没有预料到这种待遇。40总而言之,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指出的,“对非虚构叙述的记载与文学作品在共同的意义上而言都是创世的,还可以说,对梦的记载也是如此”。41 在时间的进程中作品可以从虚构的状态转向非虚构,反之亦然。《圣经》对于大部分西方知识阶层来说就从历史转向了虚构。或者一个文本也可以在一种文化中被当作虚构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并非如此。42不管怎样,每一部虚构的作品,正如J.O. 厄姆森(J.O. Urmson)所提醒我们的,都伴随着整个实实在在是真实的预设的腹地。42理查·盖尔特别离奇有趣地相信如果一部作品的主要人物是从现实生活中参照而来的话你就无法拥有什么虚构。44约翰·塞尔认为一些虚构的人物是真正涉及的而另一些则是假装存在,而真正涉及的那些人物必须准确地去虚构之。一个人必须坚守历史的真相,例如,当要书写历史人物的时候。45 这一观念忽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虚构的陈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真正有所涉及的,比如那些会让你感到想吐的对狼吞虎咽整堆纸板箱的行为的赞誉,在一种将其“虚构化”的语境中如此陈述。我的意义是通过这样做它以一种从头至尾的修辞或曰观照的方法来将它们作为特征而赋予了其可动性。且这种观照的方法并不总是使自身受制于真假的判断的,不过让我们稍后再来考察这一主张。几乎在所有的虚构作品中都存在着大量确确实实是真实的陈述,不仅仅是现实主义作品而已,但关键在于他们是如何策略性或修辞性地来发挥功能的,而不在于它们的认识论形态是如何如何。一种陈述,像盖尔有益地提到的那样,“可以是真可以是假反正我们也不在乎去赋予什么真实价值”,就算有些人说这是可证实的我们也不会没事找事地去证实它。46这样去做并不会必然地导致我们丧失在此类有所指涉的陈述中关于真实价值的洞见,只不过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题写那些陈述罢了;而我们这样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所指的也就是虚构了。47 让我们重新回到塞尔吧,他以清教徒式的精神想象有关历史的虚构必然要忠实于过去的真相,因此而未能见到自由地去阐发事实的历史小说在某种层面上有可能比那些没有这么做的作品更真实。此外,虚构化历史的意图在于重新解读事实并以此来突出你所认为的他们潜藏的含义。这不需要带有一种斯大林主义的谋划。它意味着如果你在写一部关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历史小说,你或许通过考虑周到地隐瞒她在二十世纪活得很好的事实来仅仅为了强调她是一个何等典范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取而代之的是,你可以为她布置一场象征更令人满足的死亡,兴许死在一名她刚救护苏生的年轻战士的臂弯里。不久以前,一份埃及政府报通过把埃及总统放在他的美国对手之前的做法篡改了一张世界领导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照片,其根据在于这名埃及领导比那名美国先生做了更多推进和平进程的贡献。这就是让道德真理优胜于经验真理,同时也就是一步权威性的虚构化落子,即便它实际上不过是一段奥威尔式操控的冷嘲篇章。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曾表示你可以凭借着使其更不真实,或是在某些不同的意义上真实来提升一段叙事。48虚构作品能够通过创造性的虚假来忠实于现实。历史并不总是拨乱反正的,它会捅出一些不可原谅的大篓子出来。它会推举一些显著醒目的对称和可喜可贺的巧合的可能性,杀光几个人物就因为他们变得越来越有趣,频频地跑向矫揉造作与滑稽闹剧,对恶毒之人的境遇慷慨大方,为主导叙述过度地负荷了许许多多冗长乏味的陪衬情节还容忍某些无足轻重的意外来分散我们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真实瞬间的注意力。同样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真相不止比虚构更陌生甚至比虚构更虚构。没有一个关心他或她的名望的小说家会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那样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赚取他人轻信的例子在历史中数不胜数。 虚构的范畴最初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从事实的报道中区分出逐渐演变为现实的一种想象性写作的形式。你不需要什么区别如若文学还是公然非真实的。只有不太正常的缺心眼的读者才会需要把“虚构”一词添加到《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或《蝙蝠侠》(Batman)漫画上面。之后,虚构开始被心照不宣定义为与非虚构相关了,在此语境下差异遂成问题。接着,区分的不稳固性又持存了几个世纪,从诸多关键的混淆困扰之中都可见一斑。克利斯朵夫·纽认为“一部作品非虚构陈述的比重若是极大地超过了非虚构陈述的比重则不成其为一部虚构作品”,49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读者依然可以用非虚构的言说来撇开真实价值,也依然可以虚构化整部作品,虚构与非虚构的述说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它一些典范性的含义,还可以用它来使人信以为真。还有可能文学作品在一个层面上是虚构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则并非如此。不同于《小老头》(Gerontion)或《高老头》(Le Père Goriot),一篇布道辞或一段政治宣传也许想被当作真实来对待;可是它们在某个层面上也是虚构的,因为它们邀请读者跟着它们去做信以为真的行为或驰骋自由的想象。一位读者可以在她的脑海中协调地操作这两项。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允许我们全面而立体地理解人物形象,突然中止他们以便同时从诸个角度去发表意见,可以从更频繁地出场或充分地接近的层面上,使此类人物看起来更为真实,而不像大多数个人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来了而后走了。艾丽斯·默多克曾谈及我们皆生活在彼此他者生活的间隙里,但在某种虚构中这一情况是可以终了的。 当使用它们作为一场伪装游戏中的支撑之时,一名读者或许会显露出特定命题的真正认知力。“想象某种东西”,肯达尔·沃尔顿写道,“与知道某种东西是真实的是完完全全具有可比性的。”50托尔斯泰告诉我们拿破仑入侵了俄国,他确实这么做了;但是依靠着被称为小说的功效,《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还邀请了我们去信以为真这个事实,将其融合进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一对夫妇在吉姆·克雷斯(Jim Crace)的小说《随之而来的一切》(All That Follows)中“在做爱的时候还想象着做爱”。拉里·戴维(Larry David)既是现实生活中《宋飞正传》(Seinfeld)的创造者又是电视剧《抑制热情》(Curb Your Enthusiasm)中它的创造者。奥斯卡·王尔德远比后来任何的演员都更巧妙谙熟地扮演了他自己。现实可以是幻想的主题,而一个幻想仍旧是虚构的即便它碰巧地与一系列现实事件相一致。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一个真正被检举的妄想狂也是一个老是生病的臆想病患者。 所以有些东西的的确确既可以是事实又可以是虚构。再从沃尔顿这里搬一两个例子过来好了,有的人可以做她享受温暖气候的白日梦并且实际上也是如此。密西西比河在《汤姆·索亚历险记》(Tom Sawyer)和现实中都沿着密苏里而流淌。一个孩子在一种虚构里(一场游戏)也在实际上喊出“别动,小偷!”的词语,故而他的所作所为就同时是现实与虚构的。“事实可以是虚构虚构可以是事实,”沃尔顿宣称,也就是说你可以虚构地对待一个事实,将其合并在一场假装的游戏中,结果是一件虚构的叙事完全可以被用来构成经验的真实。51一个人还可以补充认为纵然在字面上非真实的陈述也会在被置换为一个不同的字面记录的时候以另一意义演变为真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吧!你们将会失去的只有你们的锁链”就字面而言并不正确,既然工人们要反抗帝国他们就要冒着危难失去许许多多的东西,尤其是,在必要之时,献出他们的生命。然而,一旦这一声明出现在政治宣言上,使它在别的意义上成为真实的那个文类的规则就在于将其转化为一段修辞性的激励。在竭力主张一种道德真理的意义上而言它现在是真实的了,亦即劳动人民只能通过联合与反抗来实现正义。 让我们暂时回到关于同时是真实与虚构的行为的问题上来。假设(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吧,不再偷沃尔顿的了)你在排练一部戏剧而你需要有人来扮演大公这一角色。瞎猫碰上死耗子——巧了,一位真正的大公心不在焉地蹒跚而至排练室中。你即刻拦截了他并请他出演这个角色。由于他对真正的大公如何表现可谓是最了解不过了,他所创造的戏剧性幻象实在是让人服服帖帖。现实暂时被征用来为幻想服务而又不终止其现实本身。同样的案例还可以适用于在一出戏里对某人的殴打。如果你凑巧对你的同行演员怀有不可遏制的厌恶感,你或许可以不用走出虚构的框架而随心所欲地、恶狠狠地对他拳打脚踢。再或者你在一出戏中要做出打喷嚏的动作,却发现你真的打了喷嚏并且还应付过去了这一部分的表演。因此你的喷嚏就同时是虚构的与真实的。我会玩一个游戏,在游戏中英国女王是一名朝鲜间谍,但我也相信她实际上就是朝鲜间谍。兴许她真的是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热带惊雷》(Tropic Thunder),里面有一群西方演员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摄制一部电影,由于拍摄电影的需要他们假装与当地人民发生了武装冲突,却没有意识到当地人民确实和他们发生了武装冲突并实实在在地攻击了他们。不过当然啦他们并未如此,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一部电影之中。 假装可不是,当然不是,仅限于虚构而已,故而也不能成为它的一个充分定义。尽管如此,沃尔顿对这个概念应用的诸多长处之一是它不会产生主观的幻想。假装在他看来主要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根据一系列明确的规则与协议来进行表现。在一场假装的游戏中,X(就说是一只泰迪熊好不好)代表了Y(爹爹)而不代表任何别的东西(虽然多样化的意义往往也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游戏中一个人所要想象的东西,和一个人所要想象的方法,在此场景下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而不能仅凭着一时兴起就去胡搅蛮缠。这一点,倒是一种令人惬意的非浪漫主义式的想象概念,没有被期望着去对任何的惯例都深感不能承受。 约瑟夫·马戈利斯声称“当一个命题为真之时一个人无法假装它是真的,并且还知道它是真的”。52格雷戈里·柯里心同理同地写道“你不可以同时做某事并假装去做此事。”。53但是在假装的特定意义上,如果别的暂且不算的话,这必然是值得怀疑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扮演侍者的侍者就是一个切题的著名案例。你扮演或表演你实际上所是之人是有可能的,正如那些令人恼火地虚张声势类型的人,他们大可以径直自我放纵地去扮演此类他们自己的形象。人类众多的行为举止都是带有这种双重性的印痕的:做某事的同时还表演着做某事。如果我们是演员,我们也是我们本身或赏识或挑剔的观众。要是柏拉图把戏剧驱逐出了他的理想国,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使得舞台演员同时成为了他们自己与某个他人,而这会对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身份认同实质的稳固性造成打击。倘若一名鞋匠开始设想他不是一名鞋匠了,政治腐败的后果也将紧随其后。 这类两重或曰分裂的意识属于我们本身与我们环境之间相互融合中的空隙。在现实与自我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这部分属于我们与世界紧密关联的特定做人的方式。这并不是什么置身事外或浮于表面的问题。我们与现实之间相应地是一种讽刺性的关系。我确实很火冒三丈,但与此同时我察觉到我自己在进行惯有常见的火冒三丈的行为表现,不由自主地遵循某一剧本尽管我所感觉到的却是全然真实的东西。观察狗狗或兔子的表现,我们会发觉它们倒并不共享这个颇具讽刺性的意识模式,不知道算是好事呢还是坏事。维特根斯坦评价道“一条狗并不能撒谎,但他也就不能诚挚”,我们大概还可以补充说他不能讽刺性地活着。很小的孩子们也不能如此,这正是他们部分的可爱所在。有些观察者就此而对整个国家得出了结论。就这一点而言,至少,虚构乃是现实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虚构使得读者既着迷于一种幻觉又同时对它未予以任何注意。因此它是一种讽刺,因此它所书写的主要是我们日常体验的本质。我们因考狄利娅(Cordelia)之死而悲从中来,尽管如此,就像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我们从未忘记我们身处于一家剧院之内。塞缪尔·理查森在一份信里写道“虚构普遍地[伴随着那种历史实在感]被阅读,虽然我们指的它是虚构的。”54 假如,同肯达尔·沃尔顿一样,你也觉得假装就是信以为真,55那么很明显的是假装与现实之间就没必要起任何争执了。设想一名歌手摹仿她自己的嗓音然后发现如果她真正地以自己的嗓音去唱的话她将使这一模仿变得更令人信服。在她沿着她唱歌的口型而动的意义上,她依然在假装唱歌,但她实际上也真的在唱歌。我有可能开着我的车并信以为真我是一位如迈克尔·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那样的著名赛车手。但我也有可能真是迈克尔·舒马赫,开着他的车并幻想着这一事实,自我陶醉地玩味着他本身的声誉带来的形象。或者我也会挣扎着要起床但同时假装我要这么做,通过装模作样地去做即可。有一首老歌叫做《自欺欺人》(Only Make Believe)其中有一行唱道“大概也会信以为真我爱你,/可要是说真的,我真的爱你”。 二十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文化事件之一发生在1920年的彼得格勒,那时候数以万计的工人、士兵、学生和艺术家再度参演了冬宫风暴。这一场表演,同时由部队军官与先锋艺术家所策应,持续了数日,动用了真枪实弹乃至于超级战舰。很多参与了这场戏剧性虚构的士兵与水手都不只是加入了他们对这次事件的纪念,而且也积极地在彼时的俄国内战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革命,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所意识到的,似乎是古怪地交叉着事实与虚构的。同样的情理也适用于1916年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56 J. L. 奥斯汀(J. L. Austin)提供了一个关于假装并真正地做某事的例子,一位参加聚会的嘉宾表现得毫无节制地不庄重就为了自娱自乐,结果却发现虽然是假装的不庄重但仍旧被这一上流社会所理解为真真正正的粗俗。57这标志了他不是一位够格的绅士即便他只是摹仿了粗俗的行为。更模棱两可的大概是,奥斯汀让我们设想有两名罪犯在从事于一次严重的犯罪行为,为了分散他们犯罪目标的注意力而假装在瞧着一棵树。他们真实地在瞧着树,但虽说如此,这不过是欺骗他人的一种表演或假装而已。真实地去看别的地方是为了假装地更好。假装不是必须做着某事而实际上并不感觉到这一点。如果你能设法激发轻微真正的苦闷的话这或许能促益一幕对悲伤的演出。不管怎样,假装不必是表现悲伤而实际上并不感到悲伤。许多人,有着某些扭曲的性情或外貌,看起来满怀惆怅而心里面却乐开了花。在一场葬礼上行为举止庄重明理与仅仅看似如此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一个关于感觉的问题。你可以表现得庄重明理而不用感觉到任何特殊的东西。 奥斯汀以一种惊天动地的口吻问道,是否有可能假装咳嗽呢?你可以假装咳嗽而实际上不咳嗽,比如你在你的嘴前握拳然后无声无息地抖动你的肩膀来哄骗某个不在听力所及范围之内的人。不过你也可以做出咳嗽的声音而仍旧在伪装着咳嗽。这是否意味着存心做出这种声音来,是与自发的一阵肋骨扳紧而发出声音截然相反的呢?未必。有些人可能会存心咳嗽就为了清一清他的嗓子,而佯装则是一种社会实践与一个语境问题。(“佯装”(feigning)与“虚构”(fiction)有着同一个词根。)你肯定会想要哄骗某人,或想要阐明一种观点。某些美国人在遇到一个老烟枪的时候会装作咳嗽,那是为了表明他们的道德非难。奥斯汀有关咳嗽的那些学究式的奇思妙想是一个特别地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在哲学史中存在着更多更重要的问题。很难想象黑格尔或海德格尔会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思考那种问题。虽说如此,它还是可以给出一些有益的启发,帮助我们思考关于虚构、现实、摹仿、表演、意向、体验等等问题。难怪雅克·德里达对奥斯汀情有独钟了,在奥斯汀嘻嘻哈哈的玩笑、淘气捣蛋的逗弄、一本正经的奚落与学术规范的逸出中,想必他是瞥见了一种他本身更高卢式风格的反哲学的盎格鲁-撒克逊版本。 斯坦利·卡维尔认为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假装与真正地做某事之间的区别是非判别性的。58他的意思是那些假装害了相思病的人并不是尝试着去达到真正的相思病判别标准然而却失败了的那些人。判别标准告诉我们某些东西是什么,而没有告诉我们它的某个特定的样本是否是真材实料。确认什么可以算作害了相思病的判别标准是可以被一些人貌似可信的逢场作戏所达到的。59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她所假装的是害了相思病,而不是陷入了爱河、苦海或绝望的深渊。她满足了通常所有关于相思病行为举止的判别标准。相思病的概念,还有我们平日里应用它的方法,在此正如真实情况一样开始发挥作用。对某一事物概念的领会是独立于它实际存在与否的,也不会告诉我们它是否实际存在。有的人可以借助于佯装不耐心地对待我来教导我什么是不耐心,这与一个真实的样本毫无二致。通过阅读普鲁斯特或《奥瑟罗》我或许能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性嫉妒,而且也更不痛苦地多。 一边假装一边毫不知情似乎很难。但一名贝尔法斯特的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在北爱尔兰动乱期间关注着忠诚分子的准军事部队,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地便操起了英式口音。或许假装与现实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非此即彼的差别。毕竟,假装,也是去做某件真正的事情。 假装去假装也是有可能的。我也许真的咳嗽不止但我却攫住了我的喉咙表示我不过是在戏剧性地表演罢了。或者想想,通过荒唐而夸张地表现受伤的情感,我或许想要掩盖我的的确确伤痕累累的事实。一位小说家是有意识地假装去假装的,因为他理应说服我们某个虚构的事件是真实地发生了的,并且还知道我们不会相信他的鬼话。浮夸地表演情感的受挫是一种特意使它疏离于假装的假装,由此一部文学作品可以表明假装它所记载的故事确实发生过的非现实性,这可以借助于它的事件明显的令人难以置信,亦或可以借助于高度的精雕细琢,还可以借助于它的语言的夸大特质。 A.P. 马蒂尼奇与阿弗拉姆·斯特罗觉得一篇以“从前”开头的故事不是虚构的如果它接下来发生的是“在一个又大又白的房子里,有一位叫作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美国总统在他年逾半百的时候因为表现地像是一个青少年而被人弹劾。”60但我们知道这或多或少是真实的事实并会不必然地阻碍我们将其当作虚构来看待。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阅读虚构的时候,我们通常信以为真我们所知道的是真实的东西。措辞如“从前”者是一种惯常的标记用以暗示读者不要太介意有关“这真的发生过吗”之类的问题。这样的设计就为了将行动放回到一种寓言的、准传奇式的领域之内以偏离当下,而它的真真假假则几乎是不确定的乃至于不怎么同我们的阅读相关联的。 肯达尔·沃尔顿,他写过一本近几十年来关于虚构理论的最具原创性与冒险性的作品,在其中他发现当一名读者对虚构中所描写的一位值得怜悯的历史人物而感到悲从中来之时他或她既是“虚构地”又是真正地悲从中来。61“[一名读者]实际上知道什么是虚构的,”他评论道,“并不能……影响她知道这一虚构是真实的”。62他的意思是一名读者大概知道那条美人鱼并不存在,但是却会接受这个特别的故事的真实存在。狄更斯的《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沃尔顿认为,在读者被虚构所期待着去相信巴黎是个真实的城市的意义上来说,使其成为虚构的巴黎是存在的。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有可能会在流传之中自动地被苏格兰人巧妙而精微地虚构化了。一份声明对一个现实的人或地方来说可能是真实的但也同时是虚构的,或者也有可能是虚假的并同时是非虚构的。“伦敦”这个名字在一部小说里是虚构的,因为真实的城市要进入文本的话只有在相关特定的条件下,尤其要以特殊的方法被编辑、组织与“聚焦”(用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术语)之后才有可能。 所以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在对诗歌的评价中,说什么“想象的花园里跳跃着现实的癞蛤蟆”,其实并不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事情远非如此简单。约翰·塞尔主张虚构既涵盖了真命题又涵盖了假命题,而一名作者在书写虚构的过程中可以立下“严肃的”断言。63不过他绕开了如何去鉴别此类断言的问题。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白,亦即宣称了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在作者方面是一个真正的断言。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啊?文学艺术作品会以它们的叙述者之名做出某些连作者自己都不信任的论述。纵然托尔斯泰相信他所写的,他也不一定就把它当做一种真理来维护。他或许只不过想要凭借着对多愁善感的体现来为小说增加道德与美学向度上的分量罢了。又或许他在写下这一句的时候是相信的,但十分钟后他变心了。还或许他都没有问过他自己他是否相信这一点,再或许他对这种事实抱着真正的不可知论的态度。不知道你自己相不相信某些事物并没有什么不正常。哲学家时常趋向于设想信念是比它们通常所是的更为清晰的东西。 如其不然,托尔斯泰或许会相信他曾经相信这一论述,而事实上却是在自欺欺人。又或许他给予这个评论一点临时的信赖但也保留他最终的判断。同样地,读者,也可以藏有一点小小的看法关于她是否相信这一宣称,或她是否真正意味着相信它,或是否和小说人物在同样的层面上去对待这一观点会更好。又或许她自己开始了对这一见解的接纳而没必要相信托尔斯泰也是如此,或他是否相信这一点对她而言确实是事关重大的。64如尼古拉斯·沃特斯托夫(Nicolas Wolterstorff)所表达的,“一部虚构作品用不着指出事态的虚假,作者也用不着相信它们是虚假的。他可以真心实意地想象它们都是真实的,并且它们真的有可能会是真实的。使他成为一名小说作家的正是任何东西他都不断定而有些东西他将其呈现。”65一名虚构作家在沃特斯托夫的眼里并不是假装而是呈现——提供某些东西来让我们思考而根本不加顾及它的真实价值。彼得·拉马克恰当地提醒了我们这种举动并不仅限于虚构。66我过一会儿再来为此观点做一些描述吧。 一名作者会从他的叙事人物的背后暂时走上前来现身说法。托马斯·曼(Thomas Mann)就在《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奏响尾声之时深深打动人心地冒出了头。尽管他反复申说他现在要对他的读者进行坦率而诚挚的致辞了,但我们怎么知道这不仅仅是虚构游戏中的又一步棋子呢?在《李尔王》(Lear)中莎士比亚出来告诉我们“成熟就是一切”的时候他是认真的吗?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吗?此类论述,终究吧,有时候反映的还是一个不可靠的角色或叙事者的思考。波洛涅斯(Polonius)对他儿子言简意赅的忠告有多少是成熟的莎士比亚式的智慧,有多少是落后于时代的废话连篇而又有多少口是心非潜藏在二者之间呢? 此番道德话语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表达作者的观点,但这并不是它的重点。重点在于它要被“虚构化”,被对待为总体设计中的一个元素而不能为了单独的判断就从它的语境中被抽象出来。我们大概的确能发现波洛涅斯的劝告是切实有益的,而且这大概增进充实我们对所讨论的文章的体会。获悉一部作品的道德观的由衷与深邃大概会加深我们对它的体会。但就算我们发现了它是由衷而深邃的,我们这样观察的方法所依据的也不过是形式上的构成。而这是不同于在某一天我们邂逅了他们然后发现波洛涅斯情感的切实有益的方法的。 “读者想象出来的活泼生气,”沃尔顿写道,“也许会被他想象为真实的知识所夸大。”67我们知道在布加勒斯特这个城市逛来逛去会很危险的事实将会在我们以一种虚构的形式遇见这一事实的时候为我们信以为真的行为添加实质上的基础。想象与现实是可以和衷共济的,而不必非剑拔弩张不可。对于一部作品的道德维度与其经验维度来说也是如此。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最典型的虚构命题既不能是已经证实的也不能是有所篡改的,因为它们是实际上的伪命题,比如“洛克已经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在跑了”,这一命题在这个理论的观点看来所表明的只是做了一个断言。无论如何,道德观,有时候能被判断出真假,至少在某人是一名道德实在论者的时候。我说“有时候”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哀叹时间的流逝或期盼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乃是非真非假的。另一方面,一部小说有可能暗示性地持有某些人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观点,而这一点不可否认地是真的。然而,如果,它看起来似乎认为这是人类值得关注的唯一真理的话,它也有可能因为它那扭曲的道德视野而遭受谴责。我们可以确信这是不对的正如我们可以确信蒙特利尔的冬季天寒地冻坼,或确信克雷是个比劳斯更美丽的爱尔兰城市那样。W.G. 塞巴尔德(W.G. Sebald)是所有现代英语作家中成就最为惊人的几个之一,其本身也成为了这种引人注目而几乎不存在什么负面效应的批评的论题;但尽管如此或许还是会有人想要弄明白是否他从不间断的对现代历史所作的阴暗的描绘并不是过度而片面的。 如果那种批评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继续欣赏一段文学艺术就算我们觉得它总体视野中的道德面留有着缺憾,这一态度要是撞上塞缪尔·约翰逊可就会被当作品行不端了。存在着严重的道德保留的文学篇章是不会让约翰逊感到享受的。他找不到一部作品是在美学上引人向往而在道德上引人唾弃的。这与现代所形成的反照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把塞缪尔·贝克特列为一名天才艺术家的人中没有几个会将其归因于他对人类存在所持的阴郁的看法,甚至有些人会视其为道德衰弱。而更少会有人为这一观点的冲突而受到感染。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贝克特式的世界观实在是太令人不快的话,他们进一步将会发现自己穿了一双约翰逊的靴子而且确然无法欣赏他的作品。在《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的伦敦首演期间,一大群愤愤不平的观众呼喊道“这就是让我们付出了一整个帝国的那种东西!” 所以这一维度是有界限范围的。拉马克和奥尔森主张一部文学作品道德视野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对其品质的赏析,我刚才也已经表明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68艺术文学作品鼓吹令人厌弃的道德行为如种族清洗者不太可能凭借着他们形式上的光辉壮丽就足以解救他们自己。一部作品也有可能因其道德价值与声誉而在修辞效应上事半功倍——这是门罗·比尔兹利所忽视的另一点,对他来说文学价值全然依赖于一部作品观点的正确与否。69确实有些时候没有任何东西比真理更能令人信服的了。 同样地,我们常常赋予一名作者经验上很大的施展空间就像在道德上那般,不过也并不是绝对如此。可以说文学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去撒谎或犯错的地方。因为一部文学作品与之俱来的内在暗示即为“将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当作意向来对待”,一名作者的事实错误很容易被当解释为有意为之,由是而成为了文本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始终如一地拼写错误“弗兰肯斯坦”这个名字,如W.B. 叶芝(W.B. Yeats)所习以为然乃至于几乎不可能不拼错的行为,大约会被误以为有什么预兆性的象征意义存乎其间。虽说这样,还是会有不证自明的错误的。前不久,英国有一个家庭哀悼一名被谋杀的孩子并为他竖立了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这样的言辞“过去没有哪一天/我们坐这里哭泣”,这想必不是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吧。倘若你犯了什么阿诺德·爱森伯格(Arnold Isenberg)称其为一个“轰动一时”的错误,70那么你的作品会为之而遭到艺术般的回应。就如读者逐渐发现作者竟然真的以为蜘蛛侠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一样,他的小说的可信度将蒙受沉重的打击。 2 在文学哲学中对虚构性最具开拓意义的解读之一的当属所谓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了。大量关于这个论点的影响深远的早期论述都可以在理查·奥曼的一篇经典的论文里被找到。71在这一理论中,文艺作品“不是一类特定的语言(language)而是一类特定的言说(utterance)”。72它们是对现实生活言语行为的模仿,尤其是讲故事的言语行为;但是借助于对一个合法有效言语行为的通常状况的违犯,它们以一种“不恰当”的方法模仿了此类言说。73我们不会问一个虚构作者,譬如,她是否准备好了为她的报告的真实性担保到底,亦或者她是否真挚诚恳,再或者她是否有资格践行她的断言。何况作者也无从确认读者的“领会”在任何特殊的情形下是否都有所保障,J.L. 奥斯汀视这一点为完成言外行为的基本要素。 虚构文本往往被认为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双重性。它们是摆出对世界正解姿态的文字幻想。言语行为理论以一种提示性的新方法重新系统地论述了这一双重性。过去曾被设想为语言与现实之间的一个间隙的东西现如今成为了两种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分。一部文学作品是缺乏所谓的言外之力的作品,通常只是依附于它被塑造而成的句子之中,故而也就是一种脱离常规的言说。和俄国形式主义者大致相同,言语行为理论家表达一种本质必要的否定性或反常性的文学解释,认为是寄生于所谓的普通语言行为的。 一名读者,看到“小说”或“短篇小说”这样的词语,就知道不该去查究什么文本中所描绘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真实存在,而所有相关的信息又是否都容纳进去了,还有荷尔德林在写《许配里翁》(Hyperion)时候的情感又是否恰巧真挚而热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作者假装汇报话语而读者假装接受假装。”74支配真正言语行为的规则在遭遇文学的情况下将被悬置,尽管奥曼承认这一点在玩笑与其它言语形式那里可能会和在契柯夫(Chekhov)或曼佐尼(Manzoni)那里同样适用。因而,它并非文学的一个充分条件,至于是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让我们稍后再谈。 我们可以转向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来分析这个理论的一种特别精明实际的公式化表述,他声称“虚构中的断言不应被严肃对待,它们不过是虚拟的断言而已。即使是思想也不应被严肃对待,例如有关科学的思想;它们不过是虚拟的思想而已……逻辑学家没必要去考虑虚拟的思想,正像物理学家,那些要着手于研究雷的人,不会去留心于舞台上的雷。”75并没有很多批评家坚持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关于他在创作诗篇的时候被他的敌人所弄瞎和包围的那些刻骨铭心的诗行不应被严肃对待。我们严肃地对待它们虽然我们怀疑它们在事实上并不是真的。它们并不是单纯地在那里为我们结出审美满足的果实,即使它们真的这么做了,那这么做的方式也是与思索本身的哀伤与坚持不可分离的。称呼一种陈述为一个伪命题,假如有人觉得这是值得做的,那也应该是去表示它的认识论状况的特性,而不是将其视为空洞而不予理会。所谓的伪命题如“仁慈的品质并非勉强”者比名副其实的命题如“这只沙鼠看起来色泽不佳”者有着远为强大的感染力。 就为了使他自己与文学更亲密合拍一些,弗雷格在同一篇经典的论文里评价道,“就某种意义与含义而言”,那些个“真理问题[在阅读文学之时]会导致我们为了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而放弃审美上的愉悦”。76他由此而以一种科学性的偏见确信真理与科学性的真理是一模一样的。但其他类型的真理是存在的,如弗雷格自己也意识到的那样,还有对它们除了科学研究之外的其他研究方法也是存在的。你不需要一个实验室来检验奥菲利亚是否发疯,或E.M. 福斯特(E.M. Foster)的箴言“拿进来比给出去要幸福”是具有巧妙的洞察力呢还是只不过油嘴滑舌而已。杰里米·边沁在他的文章《奖赏原理》中写道艺术的目的是去促发激情,在这一方案中任何有关真理哪怕一丝一毫的暗示都将是致命的。他也是这个样子,觉得真理就是真实之理。就算我们把这个词如此这般的限定一番,说什么真理是一切激情所毁灭的原因也是不真实的。边沁没有思忖到任何东西都无法像真理那样去促发激情的可能性。 言语行为理论和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文学的论述之前是有关联存在的。深思熟虑一下,比如说,它针对我们关于虚构的论述所能赋予的启发。从一种言语行为的立脚点去看,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信以为真,亦即读者知道某些惯例是无效的情况下去信以为真它们是有效的。此外,因为一部作品的陈述只不过是对真命题的模仿,所以也就并不会去从事奥曼所声称的“世界事务”,它们是非实用性的;这也正吸引了我们去给予它们那种戒备的注意力,而一般说来我们不会对垃圾回收周期变更的通告去留心太多。它还邀请了我们以一种当上述通告出现的时候不太会被应用的方式去普遍化它们的意义,让我们衡量它们的道德内涵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当作一份经验性的报告来处理。 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存在于言语行为理论、虚构、信以为真、道德真理还有非实用性之间。譬如,言语行为理论与虚构真实之间就有着一种关系。文学言语行为属于更大类的言语行为亦即施为句(performatives,亦可译为述行语、言有所为、施事句等),它并不描绘这个世界而是在说的行为之中做成某些事情。问候、诅咒、乞求、侮辱、威胁、欢迎、承诺等等皆可归入这一范畴。例如你说承诺就是去做承诺;宣布新百货商店的开张就是去开张。体现在一个词语上的意义也以同样的方式体现在行动之中。一部虚构作品亦然,是由一系列除了阐述的行为之外没有存在的真实性所构成的。或者就算它们有吧,也不都是那么重要的。施为句是最能发挥其强有力的实际效用的语言,不过也是最自主的语言;而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与虚构之间又存在着有趣的姻亲关系。虚构,也一样,恰在说的行为之中实现了它的目的。一部小说中的真实就是散乱无章的行为自身所产生的效果这一真实。然而它却可以对现实造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 再者,正如述行行为不能被断定为是真是假因为他们不是对于世界的断言,虚构的表述也是如此,在言语行为理论中仅仅作为此类断言的模拟或戏仿,同样是无法成为真/假判断的人选的。珊迪·帕特瑞(Sandy Petrey)写道“当我们考虑述行行为的时候真伪并不在点子上”,77因为这种施为句——问候、诅咒、乞求、拒绝等——并不是命题性的。尤为相似的是阿瑟·C·丹托(Arthur C. Danto),他在“未达成目标的句子与那些没有目标去未达成的句子”之间看见了一个区别。 可是汇报、勾勒与描述之于述行行为就像是打赌、拒绝或谩骂那般。它们,也一样,做成了某些事情。事实上,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界线划在述行与奥斯汀所称的表述(constative)亦即对世界的断言之间。其实,奥斯汀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承认了两者的区分应当视情况而定。在一种局面下的表述到另一种局面下可就不好说了。更何况,表述句与施为句的相互依存不止停留于宣称事物其自身如何是述行行为的这一层面上,还因为施为句不言而喻地容纳了对事物之如何是其所为的解释。倘使它们能够介入这个世界,通过某些重大时刻的许诺或最后关头的警告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它们也就必须把自己交给这个世界。对政府毒死全体老年人的计划进行公然抨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它现在因太麻烦且又太贵的原因而延迟了这一方案的实施。承诺给你一只来自马恩岛的紫斑蜥蜴作为一份圣诞礼物是毫无用处的如果马恩岛根本就没有紫斑蜥蜴,或者说关于这一点在哪都一样。 奥斯汀后来部分发现的是表述句正如施为句那般有它们所适用的条件。有关世界的命题会像述行行为那样“容易不妥当”,而不仅仅是容易不真实。79相反,施为句如威胁或谩骂者可以是恰如其分的只要它们的内容正常可靠就行(它是一个明白易懂的威胁?),需要的只是对事实的吁求。结果到头来,奥斯汀认可了这两类话语间的差别在他的手上瓦解殆尽。他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是一件“自我耗竭艺术品”,斯坦利·费什如是评价道。80它是解构的老生常谈。81奥斯汀指出,我们所生产的极少数言论会简简单单地是真假分明的。文学批评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我们在下一章还会碰到他,声称表述是“科学性的”而述行则是“戏剧性的”,但他却还承认它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差别。定义是它们本身的一个象征性行为,而所有的描述性术语都包含了决定、选择、排除、偏袒等等。82 表述句与施为句难分难解在乔纳森·卡勒的主张中是很显然的,撒谎不是一种像承诺一样的述行而是对虚假的一种陈述,所以也就是一种表述。83但撒谎不只是一种虚假的陈述而已。我或许会宣布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是一个祖鲁人因为我真的相信他就是的,这不能算一种撒谎。就算知道一个人的陈述是虚假的也无法去做出什么要紧的区分。在我们都明白你应该三个月前就到这里的时候假如说“我的上帝啊,你太早了!”也不能算是一种撒谎。形容你自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轮回转世(Alexander the Great)还是不能算作一种撒谎,反正没人会以为你这么说是认真的。撒谎是一件有意行骗地去言说虚假的事情。那么这在奥斯汀的术语意义上就不太确切地算是一种述行了,它当然包括了做某些事情。同样当然的可能是,以这样的方式讲述真相就像表明你所说的乃是虚假一样。 在更基本的意义上表述语是依赖于述行语的,反之亦然。我们靠展开含义来刻划特性、验证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读后感(六):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第二章:什么是文学?(一) 1 现在我们可以从最高存在的上帝下降到更为世俗的问题上来了,究竟被称作“文学”的东西是否真实存在。这个简短附论的要点在于证实某个问题的险境。这个晦涩难解的问题即不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政治上,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某种共同本质。 几乎是在三十年前,在《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中,我作为一个坚定的反本质主义者辩论了有关文学本质的问题。我坚持强调文学毫无本质可言。那几篇文章清算了“文学”没有任何独特的固有性质甚至连相互之间的共同性质都没有。尽管我仍将为此观点而辩护,我如今更清楚的是,我当时的唯名论并不是唯一应对本质主义的选择。文学没有本质并不意味着文学这个范畴就完全没有合法性。 斯坦利·费什写道:“关于‘虚构作品’的范畴最终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特性或一系列性质能让所有虚构作品共同拥有或组成必要而充分的一部虚构作品的条件。”2选项已然清晰:要么一部虚构作品有本质,要么这个概念就是空洞的。简而言之,费什是一个倒立的本质主义者。他相信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没有本质的事物并非真实存在;只是阿奎那认为事物确实有本质,而费什认为它们没有。在其他方面他们的观点简直如出一辙。和费什穿同一条裤子的E.D. 赫施(E.D. Hirsch)[1]论证道:“文学没有独立的本质、美学标准或别的东西。文学是一种对语言作品随心所欲的分类,它并没有呈现出任何别具一格的共同性质,也不能被定义为一种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2]。”3在本质主义与变幻莫测二者之间,我们又一次被逼着着面临霍布森的选择(Hobson’s choice)[3]。 针对这一非此即彼的困境,最具说服力的依旧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谓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理论。此理论的首次登场是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53)之中。这是迄今为止哲学能够提出以应对差异性与特性问题的最启发人心的解决方法;而果真如此之大的间隙也没能够断裂盎格鲁-撒克逊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话,它可能也将保存后结构主义者对差异性的狂热膜拜。因为在后头更极端放纵的行为也是常有之事。维特根斯坦走出了值得赞颂的一步,他邀请我们去思考所有游戏的共同点,并得出它们之间没有共享同一种独特要素的结论。相反我们发现的是“一个相似点纵横交错的复杂网络”。4于是乎他极为天才地将此缠结密切关系的网络比喻作一个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似性。这些男人、女人和儿童也许看起来非常相似,但这却不是因为他们全都有外耳道多毛症、一个蒜头鼻、一张垂涎的嘴或一副急躁的暴脾气。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会有上述的一两个特征,但另一些人则没有;他们之中也可能会有人具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但不排除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个别的身体或气质上的特点,等等。这意味着同一个家族中的两名成员也许没有任何共同的特征,但依然会因其他成员作为中介而被联系起来。 文学理论家们很快便借此典范之光来照射自己的关注点了。仅在《哲学研究》出版的四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查尔斯·L.斯蒂文斯(Charles L. Stevenson)[4]已运用了此理论来阐释诗的本质。5随后莫里斯·威茨(Morris Weitz)[5]在反驳艺术能被定义的观点时也引用了这一思想。6罗伯特·L.布朗(Robert L. Brown)和马丁·施泰因曼(Martin Steinmann)[6]也诉求了家族相似的概念来迫使反本质主义者指出“没有任何确定而充分的理由可以把一段话语当作艺术作品”。7科林·莱亚斯(Colin Lyas)[7]列出了一组文学限定的性质,并说任何定义为文学的作品必然例证了上述的某些性质。但不是每一部所谓的文学作品都会彰显出全部的性质,而且任何两部作品都没必要共同分有任何一种性质。8为什么我们称一部作品为文学,这与我们又授予另一部作品此称号的理由也许毫无瓜葛。约翰·R.塞尔(John R. Searle)[8]在《表述与意义》(Expression and Meaning, 1979)评价道文学是一种“家族相似概念”。9最近,克利斯朵夫·纽(Christopher New)[9]又将此见解排演了一遍:在他看来,“所有文学话语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文学话语相似,但它们之间的不可能都以一种方式相似。”10就此而言,彼得·拉马克(Peter Lamarque)[10]指出任何作品都不需要靠显示一组什么固有的性质来使它们赢得文学的尊号。11 这一典范的足智多谋很难被否认,并且它的泽被后世也非止于文学而已。它是怎样地启发了我们将如此显而易见各具异质的作品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尼采的《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艾耶尔(Ayer)的《语言、真理与逻辑》(Language, Truth and Logic)[11]还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聚集在同一个话题下啊? 祁克果(Kierkegaard)和弗雷格到底有什么相同之处?家族相似性既不诉诸永恒的本质也不偏向于权力专制的影响就回应了这一质疑。世界上的事物存在之间的相似性必须包含有真正的特性。外耳道多毛症和蒜头鼻不只是“构念”(constructs),不只是权力、欲望、兴趣、话语、阐释、无意识、深层结构等等的作用而已。但我们依然可能同时称呼弗雷格和祁克果为哲学家而不需要他们分有任何共同的固有特性。因为称呼他们二者皆为哲学家并不取决于此类特性,而是因为我们方才所看到的,某一种类中的一个成员可以借助一系列中介而与其他成员联系起来。 更有甚者,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12]论证说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任何怀疑本质的看法,而他所做的正是去复兴本质。12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到,本质是被语法所解释的,这即表明了语法规则对我们运用言语来解释何为事物的方法的支配。毫无疑问,这与阿奎那神圣天授的本质概念截然不同。那些执拗类型的本质主义宣称一件事物作为一个特殊种类中的一员自有其确定的某种或某些性质,此性质必要且充分地决定了该事物的归属种类。对一种强有力类型的本质主义来说,这些品质决定并解释了此事物的所有其他品质与表现。13但是鉴于任何成员的特性都是如此万千各殊,其实并不存在那种类型或特征可以完全去同一化每一位成员。正如我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的所作所为那样,为一种更温和版本的本质主义辩护依然是可能的,但硬要吞下这种教条式一板一眼的版本只能是过分地令人感到如鲠在喉罢了。 文学或虚构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以何者作为自身的对立面,也就相当于安逸闲适的观念寄生在劳动力剥削的概念之上。但此观念在世代交替之中也是尤为不稳定的。文学的对立面也许会是纪实写作、技术写作或科学写作,或被当作二流水平的写作,或是没有激发我们想象力的作品,或是没有从某一文雅或上流社会氛围中诞生的文本,或是那些没有启示我们屈膝于神性的东西,等等。 并非所有的文学哲学家们都竞相认可家族相似理论。彼得·拉马克恰当地指出相似性可以保持任意两个客体之间的关系,但也因此必须是“意味深长的”(significant)相似性。由此,他质疑道,这里包含了一种循环性,即将什么当作意味深长的相似性“似乎预设了而不是阐明了文学的观念”。15这种情况令人颇感模棱两端。斯坦因·豪根·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13]在一部标题可谓一厢情愿的著作中以保守的理由反驳了家族相似这一典范,称其过于放水——因为这种构架重叠交错的要素必然会导致文学延伸到他认为是非文学的范围(例如流行小说),最终威胁到了文学创作的价值观。16我们稍后再来探究这个暧昧不清的概念。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家族相似类型的定义在其边缘实际上有些许裂缝,这肯定不会为纯文学论者所接纳。 拉马克正确地强调了成问题的亲缘关系必须是意味深长的,并且正确地认定了回避这一问题是危险的。所谓的文学作品之间有多如牛毛的共同特征(比如说谐音,或者倒叙,或者戏剧性的悬念)却几乎无法构成文学自身的范畴。此外,还有一种臭名昭著的反对家族相似理论的见解。那就是宣称如果人们不能讲清楚这成问题的亲缘关系,那它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观念,因为任何客体对象在任何层面上来讲都可以与任何其他客体对象相似。17一只陆龟与骨科手术相似,因为两者都无法骑自行车。然而设使给岌岌可危的相似性一个称谓,我们好像又回到了一件事物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情形上来了,而这正是家族相似观念以为自己已然处理了的问题。反之,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将谈论的层面从个体存有迁移到一般范畴。比如说,个体存有并不都需要具有相同的特殊性质来让自身归属于某一特定种类;但种类自身是由某些性质构成的,个体存有起码要显示出这些性质之一,才能才算作是此种类中的一员。不是史密斯家族中的每一员都必有一只蒜头鼻,但蒜头鼻是我们将史密斯们认作一个家族的一种途径。 当涉及到某些现象之时,家族相似方法很难说有太大的启发意义。拿艺术的范畴为例吧。我们已经知道从家族相似观点来关照时,让每一件我们称之为艺术作品的客体对象都表现出一种或一系列相同的性质是毫无必要的。这类特征自会重叠交叉之。可是要以此来定义艺术,则非得能够例举出组成此一类别的共同特征方可;而事实上艺术是由一系列难以名状且漫无边际的客体对象组成的,要定义地言之有理简直比登天还难。如今很少有艺术哲学家会满足于说艺术能由内在固有性质来定义,或者说具有某某性质即可充分而必要地归于艺术作品的行列之中了。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14]所言不虚:“艺术作品并非自然种类。”18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认为定义艺术尽管可能,但实际上却倾向于定义艺术功能性或体制性的本质的原因之一。 任何艺术的功能性定义将自然而然地解释人们为何在其作用与影响的多样性面前望而却步。某些事物,比如说勺子或开瓶器吧,以其功能来定义它们是相当简单的。就算纵观历史也可以说它们的功能始终是保持稳固的。但文学的功能史却是飘忽不定的:从巩固政治权力到崇拜万能真主,从维护道德教育到例证超验想象,从美代宗教到辨析大型经济腐败之利弊。自浪漫主义以降,艺术作品最为至关重要的功能之一即其功能所具有的光芒万丈、几乎是无与伦比的自由。故而,艺术作品因其展现而非说出的价值来绝对地谴责整段从奴隶文明到实用文明的历史,批判交换价值与计算理性。由此看来,艺术的功能是它不需要一个功能。 要说一首俳句、一名战士装饰的面具、一段芭蕾舞脚尖旋转和十二小节蓝调有共同的所谓美学效应还是可信的,但我们很难看出它们一齐分有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内在品质。也许它们揭示了间或被叫作“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15]或整体式设计。即便如此吧,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现象却并没有这样的表现,而我们同样给予了它们艺术之名。还有一大堆客体诸如铁锹和拖拉机等也表现了有意味的形式但一般很少被视作艺术品,除非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这里。 无论如何,文学在大体上是一个没艺术那么难以名状且漫无边际的现象。一部犯罪惊险小说和一首彼特拉克十四行诗很少有什么相似点,但相比厚涂画笔、大管独奏和芭蕾滑步此三者来讲,二者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看来家族相似性也许在人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里更容易被辨认清楚。依我所见,当人们称某一段文字是文学之时,他们通常在大脑中有如下五种想法之一或者其中几种的组合体:他们的“文学”意味着虚构作品,或是与报导实证事实截然相反的内省人本体验的作品,或是极为鲜明地、隐喻性地或自觉性地运用语言的作品,或是不像购物清单那样实际性的作品,或是一段被高度评价的文字。 上述的范畴其实都属于经验领域,而非理论范畴。它们来源于日常的判断,而不是基于对此概念自身逻辑的研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些虚构的、道德的、语言的、非实用的和惯常的要素。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些性质越多地有机结合在一段特别的文字中,人们越倾向于授予其“文学”的头衔。我们或许会注意到,我列举的几个方面甚至都不全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如此谈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只不过是去谈论其语言、道德观、虚构可信度等因素而已。它并不能够分离出这些特征。稍后我们将看到文学性的其他方面也在某些重要意义上互相影响并且呈现出有饶有意味的并列关系。 整合了诸种要素的文本——如《奥瑟罗》(Othello)或《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一般会被当做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但没有任何被纳入文学的作品需要符合以上所有的尺度,而这些特征之中任一的缺席也不足以将此作品从文学范畴中除名。以此看来,没有哪个属性是文学身份所必须的。有时,其中某一性质的出场或许就足以让我们将某段文字叫作“文学”。但情况也并不总是如此。但没有任何单一的品质能够保证一部作品的文学身份。这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性质可以构成文学的充分条件。 人们也许会称一部作品为“文学”,纵使其道德肤浅,但它毕竟是虚构的且措辞别出心裁;或虽然是非虚构的,但它被赋予了意义重大的道德见解并且描写十分细腻;或既非虚构,道德观也很浅薄,但描写地精妙绝伦而且没有任何直接的实用目的,等等。有些人或许把文学当做一种实用而措辞绝美的文本(比如说在宗教仪式上吟唱以驱逐恶灵的咒语),另一些人则可能会考虑到此颂歌的实用功能过分地超越了其修辞上的诱惑力。一本由纳粹魔掌下的生还者记的日记[16]或许会被纳入文学之列,因为它具有历史价值,尽管它并非虚构且描述地实用(我们不妨说,保留它是为了让公众记住历史)而又耸人听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各类变换的排列组合皆有可能。不过也并不是想把什么叫做文学就能够怎么样的,即便雪莱(Shelly)期望能把在纲纪废弛之中创造出和谐的议会条例冠以诗名,那也只能是徒劳而已。更加中肯的有理性的人自然将为议会条例冠以意识形态之名。 “文学”一词有着众多形形色色的用法,这不并是说哪种过时的用法都是可以适用的。一个火腿三明治在后现代主义者最宽大多元的意义上也不能算作文学。不过“文学”一词的用法确实在家族相似性的意义上重叠交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大异其趣的作品诸如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7]的《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 1979)、纽曼(Newman)[18]的《为吾生辩》(Apologia pro Vita Sua, 1864)、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19]的《世俗谬误》(Pseudodoxia, 1646)、塞内加(Seneca)的道德散文、多恩(Donne)的布道辞、克拉伦登(Clarendon)[20]的《英国叛乱和内战史》(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1671)、超人漫画册、赫尔德(Herder)对国家文化的反思、胡克(Hooker)[21]的《教会组织法》(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 1597)、博须埃(Bossuet)的葬礼演讲、布瓦洛(Boileau)对诗歌艺术的论述、《贝诺纪年》(The Beano Annual)[22]、帕斯卡尔(Pascal)的《思想录》(Pensées, 1658)、赛维尼夫人(Mademe de Sévigné)写给她女儿的书信以及穆勒(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 1859)时不时的都被纳入了文学的范畴,并与普希金(Pushkin)和诺瓦利斯(Novalis)等量齐观。当某治安组织谈到要把文学移除其楼宇之时,他们将淫秽色情的书刊和煽动种族仇恨的传单归结到了这一范畴。任何种类的事物都一样,且更有甚之,混杂物、异常现象、中间状况、不分明地带、难以判定的事例也总是铺天盖地的。因为概念是从我们社会实践的粗略基础里冒出来的,其对自身边缘的盛怒自然也不足为奇了。其实概念若是没有边缘,它们对我们的用处也会大大下降的。阿奎那他自己也容许混杂物和不确定的状况。他并不是一个严格要求分清界限的本质主义者。 家族相似这一观念是动态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秉有着可扩充与转变的天赋。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守旧的批评家对它如此警惕的原因之一。让我们设想在某一特定文化中,文学首先意味着虚构。受特定神话信仰的影响,相当多的文学作品趋向于将大象从凌霄坠落的形象融入其虚构情境之中。要不了多久,这个形象或许就会成为文学自身的构成要素之一。接着将会有激烈的争议去讨论没有表现天空下着大象雨的文本到底能否称之为文学。然后,又要不了多久,对文学应当有虚构的期待将慢慢褪去,而大象形象则会与一些其他特征团结起来,这一新组合将转而构成文学的典型代表。 此处又是另一个指明家族相似模型之粗略的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断地自我解构。空间上也好时间上也罢,它所表明的都远远超越了其自身。这一繁殖力更进一步地将保守派推向提防戒备的处境。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关系无处不在。一部作品被文学性现行的标准扫地出门,最终也许会引起对整个盛行的正统观念的质疑。先锋派时尚的开创不单单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品,而是一种艺术本身的全新版本。 众多批判性的论战和诠释性的工作都被纳入到评估在某一给定的上下文里什么才能算数的活动中来了,比如说虚构的、有价值的、颇富隐喻的、非实用的和道德高尚的。所有这些范畴在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是瞬息万变的。例如在十八世纪,只有其中的一项标准——一段文字应当受人高度敬重——是一部作品被列为文学所必须的。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所谓的受人敬重在社会上引发的疑问(“纯文学”的问题)也恰如在美学上那样。与此同时,经过历史与文化的淘洗,这一主题中对连续性的高度重视也很有意思。不论其在自己的时代究竟是如何被命名的,《奥德赛》(Odyssey)、《调包婴儿》(The Changeling)[23]和《奥吉·马奇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24]如今以同种理由被称作文学。它们都是虚构的、非实用的、措辞别出心裁、寻求道德且皆被高度评价的作品。这类连续性会为那些后现代主义者敲响警钟的,他们令人讶异地视一切改变与非连续性为极端,同时又视一切连续性为保守反动。我们自己的文学机构挑出一些过去的作品中最符合其自身意识的性质也并不完全只是一个问题而已。在任何评价中,成问题的文学性质都是这些文本的中心所在。这并不改变什么算作虚构、非实用、措辞别出心裁等等性质将因时因地而变化万千的事实。 文学宝石的所有晶面正如我想要论证的那般,在其边缘皆是可渗透的、不稳固的、朦胧的,并且都易于相互融合乃至融入其对立面。去主张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意义上的虚构和非实用完全吻合冰岛萨迦的作者意义上虚构和非实用是完全没必要的。实际上,在鉴别文学的这五个维度之后,我将花大量时间来展示它们在人们手中是如何轻易就能崩溃瓦解的——我相信这一事实会暂时停下那些评论家的脚步,他们正渴盼着得出我如今已然为了某种更中世纪化的探讨而抛弃了我早期激进的文学本质观的结论。此次研讨剩余的大部分功夫将集中阐明这些因素是如何辜负了给予我们一个文学定义的希望的,不过我也希求在这一自我解构的过程中,一些路灯能够照亮人们千辛万苦去命名文学文本的努力之路。捎带说一句,当我用“文学文本”(literature texts)或“文学”之类的术语时,我指涉的是现今人们习以为常所认定的那些事物。 现代理论家的误解在于因为这类范畴有漏洞且不安定,与绝大多数的人文观念一样,他们便幻想说此类范畴没有丝毫的说服力。在你把某个种类或概念定位到一个难以实践的理想化层面后,你又把任何不足以达到此层面的想法视为毫无用处的。因为我们没有对法西斯主义或父权制的精确定义,这一观念就应该化作梦幻泡影。有关其本质的定义必须精确的信念是撒野的解构主义者操持的诸多意识之一,他们是形而上学父亲的放荡浪子。形而上学父亲害怕没有天衣无缝的定义我们将深陷混乱之渊;而为非作歹的解构主义儿子与其父分享了这一错觉:定义必须天衣无缝,不然我们就只有纯粹的不确定性。不过与其苦行的父亲不同的是,儿子在不确定性中狂欢高歌。对于德里达来说,不确定性是事物紊乱的起点;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正是不确定性使得事物能起作用。就如他在《哲学研究》中所质问的,某人不清楚的照片难道就根本不是他们的照片了?我们有必要以最细微的毫米精度来测量我们到太阳之间的距离吗?说“大约站在那个位置”是否还说得通?没有严格界限的一片领域就完全不是一片领域了?而且有时候概念上的模糊性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求的吗? 我所列举的诸多文学性质常常在人类生活的演进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小孩子首先在练习整个范围的人类声音中牙牙学语。诗歌无疑在情感上吸引了持续将力比多能量投入词语而非他人身上的造物,他们因而复归到婴儿口唇色情阶段(state of oral eroticism)[25],亦即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26]所言的“天籁口技”(mouth music)。如此说来,这种“离经叛道”(孩子气的咿咿呀呀)正是循规蹈矩(成熟语言)成立的条件,正如游戏是非游戏成立的条件,而非实用是实用成立的条件。儿童编造、幻想、发声、摹仿与假扮的行为不是并对认知的偏移,而恰恰是成人知识与举止萌生的温床。去学习如何说话也就是去学习如何想象。既然语言没有否定与革新的可能性就无法运转,那么想象以虚拟的名义而撤销陈述也正是基于其最十足的本质。 至于摹仿,儿童正是通过在某种社会形态中生活并且模仿其特有的风尚直至这些事物对他们来说变得稀疏平常来学习如何去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这也就是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将戏剧表演视作我们自然状态的原因之一。19没有摹仿就没有人的实在。其中,文学带我们复归到了日常知识与活动那游戏的根基。它让我们得以一瞥我们半随意地选择去感受与行动的个性是如何溯源于整个内化在我们语言与儿时幻想的可能性之中的。(我说“半随意”,因为一些感受与行动的方式乃是基于我们所属的物种。为深爱之人的去世而哭泣是自然而然的,这并非一种“社会建构”。湿漉漉的手帕是文化,而悲痛则是天性。)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富有创造力的作家与文学批评家更多是自由主义者而非保守主义者。这里一些与想象力有关的东西在现状面前止住了步伐。 现如今,我们可曾到达某个能够让我们谈论什么是文学而什么不是文学的地步了?非常遗憾,还没有呢。还没有的理由之一,在于我列举的上述特征中哪个都不足以独特到人们将之称作为文学。比如说,一大堆非文学类型的虚构也存在着:笑话、谎言、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声明等等。有时候一部文学作品与一个一本正经吹出的牛皮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被写了下来。一个笑话或许会富有精美的文字游戏和道德内省,在非实用目的上起了功效,叙述了一个包含令人神往的人物角色的虚构故事,且因其独创性而被高度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严格来讲,我之前所描述的任何特征都不足以将这个笑话与一个文学文本区分开来。某些人在听到这样一个漫画故事之后也许会心头溢满崇敬地赞美道:“这就是纯文学啊!” 这当然不是表示诗与笑话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从社会上来讲,它们显然是不同的实践。决定差异还是相似的远不止外观品质而已。物质背景与社会环境强制规定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区别乃是常有之事。笑话的全部重点都在于搞笑,这并不符合诸多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牢骚满腹》(The Malcontent)[27]、《伯曼克》(John Gabriel Borkman)[28]或《悲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29]自然不是为了搞笑而写的,除非是在那些独具变态幽默观的人看来。即便是漫画文学作品也很少只是为了搞笑而作,而一些斐然可观的戏剧作品,像某些笑话一样,一点也不好笑。我们并没有经常地拿莎士比亚的喜剧来让我们的同伴们无可救药地笑到抽筋为止。 一个笑话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差异可能只是功能性的,也就是说由环境所形成的。一个笑话通常不会被收入一本奢华的革制书内并被放置于书架上,虽然一名货真价实且自高自大的喜剧演员可能会抽出时间来这么做。有时候我们或许会发现要辨别一个笑话与一首诗有点难,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将《醉舟》(Le Bateau ivre)[30]与一个对某人继母的低俗嘲笑区别开来。除了异常的不规则之外,笑话明显不是诗歌。社会情境于此启发甚多。人们不会为关于继母的笑话授予诺贝尔奖。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笑话读出来以使听众在细腻的情感中无法呼吸臻至狂喜。他们不会把“笑话家”[31]写在他们的护照上,不会将自己和史蒂文斯(Stevens)或聂鲁达(Neruda)相提并论,也不会出版标题为《笑话选:1978-2008》的书籍。不论外在特性有多么相似,笑话与诗歌是不同的社会体系。我们也许会把某首诗称为一个糟糕的玩笑,但这样称呼和我们叫一名不称职的律师为一个喜剧演员的性质差不多。尽管如此,社会环境也仍旧会有不能够辨别差异的时候。在一个俏皮话和一部文学作品之间没有明晰差异的情况也是有的(斯特恩(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也许可以算作其中之一)。 考虑到一个梦洋溢着意象、丰盈着辞藻、贮藏了扣人心弦的戏剧性事件、充满了道德内省、伴随着令人神魂颠倒的人物角色且又有陶醉人心的故事情节以为动力,我们如何能加以判断小说与梦的区别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异于纳闷巧克力棒自助贩卖机到底能否思考。它们是否知道你在如痴如狂地寻找一块玛氏巧克力棒[32]呢?它们显然不知道你的想法,就像梦也显然不是小说,即便它们碰巧分有共同的外在特性。人们不会在小说中惶恐醒来,或把梦折一页角以便提示自己故事已经进展到了哪里。尽管如此,一篇释梦的文章也许会表现与文学有关的所有性质,同时真正地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临床记录的一部分。 在守卫文学与其他现象的边界意义上,这五个性质没能交出一个不可违逆的文学定义。有时候我们可以援引制度背景来界定文学,但此类援引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不容置疑。20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无法简单判定的,况且就实际上我们到底能否判定本来就无所谓。绝对的文学定义根本就不存在。所有对唯一定义的尝试在欢欣鼓舞的“但至于……”这句话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我陈述的性质只不过是些阐明文学探讨本质的参考或准则罢了,而所有类似的准则都是大致上能用而已。但大致的定义或许比柏拉图式的精确定义和无所不可主(anything-goes-ism)义都更为可取。 无所不可主义在民主立场上是个有异议的说法。它好像暗示着当人们用“文学”一词时,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自以为在讨论一个相对确切的现象,而实际上却没有。我个人倾向是比这一说法更加信任日常话语。人们实实在在地对他们口中的文学有所意识,知道文学如何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在此,我很大程度上试着去做的只不过是把这一意识打磨得更为尖锐一些。在为一个更加精确的(因而或许也是更饶有意味的)表达努力之时,谁料想,诸多问题毫无兆头地接踵而来。真是失必有得,得必有失啊。 2 既然虚构性几乎是我所接触的因素中最棘手的,稍后我将为此另辟一章。 此刻,让我们先来扫一眼其余几个判断标准吧。就从语言学上的问题开始吧,勒内·韦勒克(Réne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在他们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中坚持认为文学语言有其特殊用法,这一断言使得后来的一些追随者颇为尴尬。21现今的文学理论家们可谓抱有全体一致的信念,即文学中没有任何语义上的、句法上的或其他语言学现象上的独特可言。而若上述观点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Russian Formalists)、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Prague structuralists)和美国新批评派(American New Critics)所信仰的,那他们就是令人心碎地错了。 到底他们是不是这么想的,就是另一码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主义者以为所有文学手法都以陌生化或“去自动化”而起作用,读者因此而得以全新地感触到语言的原料所在。这听起来多么本质主义啊,就好像整个世界文学都能够穿成一串单独的策略。实际上,它的声明可名列在现代纪元中最惊世骇俗且野心勃勃的批评计划里。它自视甚高,以为偶然发现了所有文学奥秘的钥匙,并以一个单独的几近万能的手法揭晓了诗、叙事、民间传说和散文那埋藏久远的秘密。 无论如何,形式主义者所力图定义的是“文学性”,而不是文学。而且他们视文学性为一种关系性的、差异性的、依赖于上下文语境的现象。22对一个人来说是“自我聚焦”的符号或醒目而自觉的辞藻,对另一个人来说也许不过是日常习语。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促使其陌生化都无法穷尽文学策略的全部保留节目。形式主义者主要在对诗歌的研究中描绘了这一手法。他们在研究非诗歌体裁的作品时也常常求助于对此类手法的发掘,尽管发掘出来的一般是结构性而非语义学意义上的陌生化手法。于是乎他们误导了许许多多的文学理论学派,他们给予特权于一种文学体裁,然后径直将其术语套在其他体裁之上。随后我们将看到言语行为理论家(the speech-act theorists)同样地为现实主义叙事赋予了不正当的特权。布拉格解构主义者也把诗当作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所谓的“话语表述方式本身前景化(foregrounding)的最大化”。23不过对他们来说也好,对形式主义者来说也罢,只有在针对一个合乎规范的语言学背景之时,言辞表达的变形与偏离才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一切都随着语境而变化着。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形式主义理论显著地缺乏历史意识,而它们自己却趋向于在与众不同的历史境况下冉冉升起。这种境况就是文学作品不再甘愿为任何确切的社会功能而服务,由此它们也必然能够扯出一套价值观并且宣布它们的功能、基础和目的就是它们自身。故而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是独立自主的。另一个境况是当文学的基本材料——语言——发觉到自身被玷污和降格之时,文学作品必然会将系统化的暴力发泄在此不顺遂的原料之中,通过异化与转换以歪解出一些价值来。诗学因而成了一种二次方的异化,也就是对已然扭曲的媒介的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新批评派和英国利维斯派(English Leavisites)都在早期所谓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影响下生活着,并且文明地书写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正蒸蒸日上,日常语言构成了文学艺术家们的原材料。那时,语言在一连串新兴城市、商业、技术和政府的压力之下苟延残喘,而且还被迫在另一条错流的世界主义波涛里沉浮奔逐。鉴于情形的严峻,只有一次确然的危机能够带来新生。 在《文学现象》(The Phenomenon of Literature)中,本尼森·格雷(Bennison Gray)[33]相信他已抓住了他的对象的实质。一部文学虚构作品必须构成一致连贯的叙述(此声明似乎有意地要把大部分现代主义者和实验性写作驱除出文学范畴),并且要有意识地运用特殊的语言来表现某一事件的每时每刻,而非简单地将它报道出来。24故而“小猫,小猫,你去哪儿?”是文学,而“三十乃九月之天数”不是文学(这是格雷自个儿举的例子,不是我在嘲弄地戏仿)。托马斯·C. 波洛克(Thomas C. Pollock)[34]数十年前以含糊诡异的口吻论证说文学由勾起作者特定经验的语言所组成。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今天他将发现他自己大致站在了少数人群当中。25因为如今已经形成了共识,没有哪种语言、没有哪种表达上或结构上的技巧,是文学不与其他的写作所分有的。何况大量所谓的文学写作(例如自然主义小说)并没有采用特殊的偏离、歧义、借喻、反自动化、自我指涉或自我聚焦等等的手法。爱弥儿·左拉(Emile Zola)的《娜娜》(Nana, 1879-1880)或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阴间》(The Nether World, 1889)可不是因其夸耀能指的重要性而声名远扬的。同样没错的是,布朗克斯(The Bronx)[35]音乐中的隐喻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隐喻一样多。简·穆卡洛夫斯基在谈及一种“非结构化的审美观”时,说道箴言、隐喻、咒语、拟古、新词、外来表达方式等生气勃勃的技巧都可在日常用语中被发现。26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36]认为文学观念在十八世纪晚期开始涌现,它意味着某种自我指涉的或非表征性的对语言的使用,但这一看法不过是把一些特定的文学作品的类型大而化之为整个文学现象罢了。27极其雷同的是,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和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宣称文学的观念正如我们所知,其实质包涵了创造性的意识,是伴随着文学理论的想法而由十八世纪后期的耶拿浪漫派(Jena Romantics)发明的。这给我们的所有启发就是,对文学观念的界限的定义又多了一种特定的版本。28 就自指性而言,通常不被视为诗歌杰作的1979年大不列颠银行法内含了下面的这个句子:“任何涉及到这些法规中的一个法规都是一个法规在这些法规中的涉及。”既然此句本身以其作为绕口令或文字游戏而引人注目,也许有人会将它看作自我指涉的一个例子,从而在形式主义者的视角上合法化了它的文学地位。然而,一两位思想更加传统的批评家会把在文字上产生的高度影响视为对文学价值的抵制。“自福楼拜以降,”美国批评家格兰特·欧文顿(Grant Overton)以几乎不着掩饰的厌恶激动地评论道:“我们逐渐地理解了文学风格——使自己突显地像是文体的文体——是某种在小说中不太值得称羡的东西。”29作者应当朴素而实在地去写他们想要表达的事物,用地道的美式文体来写作远胜于沉醉在异想天开的法式夸耀的辞藻里不能自拔。 尽管文学理论界不太重视,这里确乎存在着一种差异,一头是以《失乐园》(Paradise Lost)或《德意志的残骸》(The Wreck of the Deutschland)[37]为例的强调修辞或自我聚焦的写作,而另一头则是纯粹地按所谓的优秀作品的规定范畴来好好写的作品。你可以用文学风格写作而不必像劳伦斯的《虹》(The Rainbow)那般开放地有点倒人胃口,也不必像《白鲸》(Moby-dick)一样华而不实地去展开行文。人们有时候为一些精美而非自觉地写出的作品冠以文学之名,而直接在言辞上自我关注的作品却被排除在外。他们也许会把某一精简而清晰的文风或是某一朴素而强劲有力的文风看作是比某一美轮美奂而独树一帜的文风更值得赞赏的。优秀的写作就像是一个人彬彬有礼那般,或许会被当成是谦逊而不吸引人的眼球——尽管在其轻描淡写到一定境界之后,如同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degree zero),将会再度吸引人们的眼球。海明威(Hemingway)是个标准案例。无风格亦可自成风格。正是如此,文学常常不能被定义为好的写作,正如多萝西·沃尔什(Dorothy Walsh)[38]所言,一切写作都应该好好写。30“好的”写作也好,发光发亮的写作也罢,都不足以拿来定义文学这个范畴。 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声称文学确有一个特性是充分而必要的,那就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种话语,其含义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暗示性的。”31但某些被归纳为非文学类的作品比某些诗歌和小说的暗示还要丰富。况且没有一定程度上的暗示的话,没有任何作品能够发挥作用。“安全出口”不言而喻地要求我们将其视作描述性的而非命令式的标志,不然剧院和百货商场就将永远都渺无人迹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比如说斯威夫特那看似白描、颇有气势、艺术性地深不可测的文风,批评家丹尼斯·多诺霍(Denis Donoghue)[39]有次巧妙地将其描述为欠缺任何伸向根部的触手。这大概算是比尔兹利眼中合格的文学吧,人们也会以此眼光来看待海明威与罗布-格里耶(Robbe-Grillet)的。无论如何,一种话语也许会在一个文化背景中载满了暗示,而在另一个文化背景中什么也不是。暗示是作品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中的功能,而非文学所固有的特性。 在自吹自擂的符号这一观念中存在着一个悖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语言与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它使我们注意到文本是写出来的文字而不是真实事物;但它又通过全方位地解除其文字的束缚以求赋予真实事物以血肉。诗性符号的悖论在于它越是浓密地组织在内,它也就越强有力地指涉向外;但这种密度同时也在其独立的意义上转化为如下现象,即因其自主性而陷入了相对松弛的状态之中以致于放宽了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联结。更有甚之,因为符号的声音、结构、韵律和声调的价值是如此触而可感,它很容易与环绕其周围的其他符号产生内涵性的关联,而不是直接意指着一个客体对象。“突出”某一标志将会“消隐”它的所指,与此同时,也将悖论性地把它提到更热切的焦点上去。 符号越是繁杂富丽,那么它所能实现的指称功能也将越强大;但是这同一个标记越是把我们的眼球吸引到其自身之上,它的本身越是真正地取代了它所意指的事物。F.R.李维斯(F.R. Leavis)热衷于带有物质现实性风味的符号(莎士比亚、济慈、霍普金斯),而对看似脱离了现实的那些自主性的符号则抱有严厉的态度(弥尔顿)。不管怎样,在令人忆起事物的馥郁幽离和质地精美的词与看起来成为了事物本身的词之间确乎有着一道分界线。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现代主义容纳了一种符号的物化,它从它所指称的事物中释放出了它本身的自由空间。是非得失齐聚一堂。在某种意义上,世界消失了,而现代派作品为其从现实的纠缠中获得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则是令人惊叹的大起大落。32相比之下,那些抵制符号自主化的诗人则选择了另一种语言,那种语言像极了(让我们姑且假设为)水果商贩的橘子和菠萝。词与词的指称之物若是化为一体,词将永远都不再是词了。 理论家们也许大多数都弃绝了文学作品有着言辞上的特殊性的观点,但他们很不情愿去抛弃另外一个观点,即在读者群中保持某种程度上的特殊的敏感。F.E.斯巴肖德(F.E. Sparshott)[40]声称我们对一种文学话语的关注点在于其内在固有的品质而非其指涉之物。33但也有一些批评家说他们无法通过内在固有的品质来辨认出文学,因为这类品质根本就不存在。斯坦利·费什正确地指出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毫无二致。他坚决认为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不过是那些我们扯了个框架然后决定付与特殊待遇的语言罢了。34正是这种特殊待遇产生了所谓的语言的内在固有的品质。这对费什来说可算不得有什么独立自主的地方。 这一观念跳过了一个未解之谜,既然作品自身无从言说,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去称其为文学。这一决定是凭什么而做出来的?我们又为何要去围绕这个文本而不管不顾另一个文本呢?这可不是因为一部作品本身的性质,既然如我所言,费什根本不信这一套。“正规的部门单位,”他大胆地以反直观的风格写道,“通常来负责作出造成影响的最典范的解释;它们并不在文本之‘内’。”35于是乎他的认识论让他无法接受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一些文本表现出的性质使其比别的文本要求更细密的阅读的观点,而这亦即文学机构需要来“决定”哪些文本应当被妥善地关注和响应的原因之一。不然就很难说这种决定到底是凭什么而做出来的;而那种没有合理的判断标准的决定,不如所谓的存在主义作品,不过是用词毫无羁绊的意识做出的决定罢了。可是比方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关于文本韵律的框架呢?或者说某些作品是虚构的呢?难道这些选择都是随意所欲的?是否文学机构也可能会随便地将《疯狂》杂志(Nuts magazine)[41]与克莱斯特(Kleist)和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的作品相提并论呢? 当然啦,耍一点小聪明的话,你能够逼着《疯狂》杂志与这一相提并论编造一些诗性的内涵出来。问题毋宁说是为何文学机构一般不邀请我们去这么做。明显的答案——那就是克莱斯特和霍夫曼斯塔尔被认为更具有文学价值——对费什来说却不适用,既然文本没有内在固有的性质,那就没有哪一部作品就其自身而言是优先于另一部的。然而同理可得,《疯狂》杂志(比如某种流行文化形体的图示)对于费什来说也没有任何比克莱斯特的作品更值得去勾勒事件背景之处,反正也没有任何内在固有的性质可言。或至少在事件背景被概述之前,它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语言品质使得其更值得被阅读或是不值得被阅读。因而,这一案例并没有给予经典的批评家任何慰藉,就像它也没有给予自身的拥护者任何慰藉一样。同时它在一开始就回避了何谓在文本之“内”的问题,好像相信“内在固有”涵义的人必然会假设涵义在一部作品之中正如白兰地在一个酒桶之中那样。 费什的理论可被看作对道德决定论的批评,但他在这里只是把做决定的个人改成了机构而已。他无法基于作品的客观事实来决定将某一文本当作文学来对待,因为在他的观点里没有此类无可指摘的客观事实可言。客观事实不过是根深蒂固的解释罢了。他并没有告知我们在特定环境下为什么它们盘踞地如此之深。这不可能因为他们是如此这般的世界的一部分,对于费什来说“如此这般的世界”本身也是解释的产物。解释生成客观事实,而非反之亦然。所谓的文本的客观事实是由对它的阅读而生成的。你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通过援引文本性的证据来支持你批评的假设,其实是用一个解释为另一个解释寻求根据。不止如此,就连所谓的文本性的证据实际上都是颇成问题的假设的产物,循环在此一触即发。证据的概念因而被严重弱化了。这世界是由一只驮着另一只一直驮下去的乌龟群。 立足于这一论点的话,下述情况将很难说得通,文本对我们为其做的阐释居然会提出抗拒,还会迫使我们在新的证据被澄清之后去修改或抛弃我们批评的假设。我们何以会对一首诗或一篇小说感到惊喜,或是推断出我们对它们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岔了弯,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文本的特性在费什的世界里并不真实到足以对我们为其做出的设想提出反抗的程度。既然我们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我们的机构对其决定性阅读的产物,那么我们在文学文本中所得出的不过是我们偷偷摸摸放进去的东西。费什在文学上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所提到的那个人观点大致相同,那个人以为自己通过将钱从一个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的方式实现了金融交易。 “文本的特性(不论它们是文学的特性还是“日常的”特性),”费什评述道,“是吸引人们眼球的一种说法。”36罗伯特·C. 霍拉勃(Robert C. Holub)[42]建议费什最起码“承认词或书页上的标记的存在……以作为‘某些先于解释的存在’,”37但他未免太大慈大悲了。对于费什来说,“一页上的标记”这种措辞简直是过分地充斥了解释。就连分号都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们作为地地道道的解释的产物的程度相当于对于《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某种异国风情的假设。无论我们解释的是什么,它必将依旧神秘莫测地隐没在康德的本体界(noumenal realm)中,因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另一个解释。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情况是将“解释”一词的诸多意蕴不甚恰当地混为一谈了。正如费什所坚持的,一切经验观察皆渗透理论(theory-laden)[43],它们变成了解释正如把马伏里奥(Malvolio)[44]当作一个商业银行家那样。因此它们并不能证实或否定此类断言。 作为一个新实用主义者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费什并没有采纳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在具体实际的语境中使用“解释”一词。我们一般在有怀疑或费解亦或非此即彼的可能性的时候用此术语,正如分号只在短视之时适用。我并不“解释”我有两个膝盖。去想象我每次看见“斯坦利·费什”这个词都要去“解释”一番就像设想当我看到某人泪如雨下之时我得去“猜想”或“推测”他有可能悲痛欲绝一样荒谬。我们能够谈及对于莫扎特(Mozart)的《单簧管协奏曲》(Clarinet Concerto)的解释,因为它们有形形色色的演绎方法,但当我眺望窗外之时,我通常不解释我在眺望窗外。 费什认为我们需要从书页中的黑色标记来推断出意义,这种执迷不悟就相当于认为我们需要从我们眼球中的瞳孔与眼白推断出一只斑马。38当我们看一个词时,我们看到一个词,而不是一系列我们解释为词的黑色标记。这并不是否认我们有时候不确定某些黑色标记到底是不是词,我们有时候也会不确定一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它在某个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感到茫然不解。(尽管一个人不可能对一个词的用法感到茫然不解除非一个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向来不会对“ziglig”[45]在具体语境中的用法感到茫然不解,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只在遇到疑问或多样的可能性的情况之时,才会用“解释”这一术语来增强某一观点的说服力。不然我的每一句言论岂非都要以“我的解释是……”这样的话来作为开端,随后这一短语将像语言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一般无法与任何东西啮合。说“那是我的老哥们塞拉斯·鲁波尔”被取代为“我的解释是那是我的老哥们塞拉斯·鲁波尔”,如此等等。也许要不了多久,这种说法就会显得枯燥乏味起来。 费什看不到疑问与解释的概念如何融合在一起,这说明他把阅读视为解释的一个过程,但却否认了任何疑问的可能性。一位读者通常能够确知文本的意义,就像她能够确知她站在了一头发疯的犀牛面前。我们被设想为需要去“解释”一串黑色标记来意指一只企鹅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可以做点别的什么。因为个体的阅读仅仅是她所属的所谓的解释群体的一个功能罢了,而对这个群体来说,意义总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是这一群体来替读者作出解释,而她自然而然地会看到解释正如它确认她能够看到它一样。读者不过是顺从于为他们作出解释的群体的代理,就像中央情报局(CIA)是顺从于美国政府的代理。从作出解释的群体的立场来看,世间万物皆为解释;从个体的立场来看,则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费什在没有解释的必要的时候看到了解释,在需要解释的时候却没有看到任何解释。39 那么对于费什来说,阅读基本上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事情了。整个阅读过程几乎都是全自动的,解释群体承担了一切而读者大可安然歇息。在如此自我嘲讽的情形之下,这类群体不会杂乱无章,他们的习以为常不会产生矛盾,他们的边界没有任何不确定性,他们也不会有任何争论或是非议,在解释群体关于文本的意识与读者尝试挖掘的意义之间也不会有任何冲突的可能性。费什倾向于把解释群体看作是难以置信的单一性术语。读者乃至于人类大体上来说是一套行为处事的方法的产物,也就是说只要你属于他们中的一员,你就不能从根本上去挑战这些老规矩。你凭什么这么做?实际上,既然人类主体是由这类体系所构建而成的,若不从自己的皮肤里跳出来,你就无从谈起什么根本上的批评。我们稍后将会看到,任何此等激进的批评,只会为了某些别的解释群体(这些群体将会与你毫无瓜葛)的利益而发,要么它就是来自抽象的外太空的言论。 费什认识论上的激进主义因此而拥有了一种颇为有趣的保守政治色彩。这暗示了在对待任何事物的问题上没有人可以与他有异议的观点。如果他能够理解你的批评,那么你和他就从属于同一个解释群体,于是你们之间也就不可能有根本上的纷争。如果他不能够理解你,那么这大概是因为你所属的解释群体与他所属的解释群体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于是你的批评也许就被视若无睹了。 认识论上的结构主义大体上把世界视为一个人解释的产物,然后便轻易地滑入了怀疑主义。这样就有可能会相信费什所说的“我们知道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关于这个世界的故事”。就此而言,如果这些故事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况且我们是如何知道这些故事的,我们又是如何知道这并不只是另一个故事?),我们真的很难看出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何以不知道这个世界。对康德主义者来说,它是不雅致地大幅度入侵我们与世界其本身之间的表面现象;对于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它是话语或阐释。这一思路断言关于“小点心”一词我们只知道这一词语本身,或是它所意指的概念,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一块糕点,不是幼稚地信赖一个词是什么这样的谬误,不是引导向一种具体化。这一思路认为词或概念是中介于我们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客体,这好像是在设想是我的身体阻止着我去接触这个世界。 此误解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索绪尔主义者、阿尔都塞主义者、话语理论家、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等人那里尤为热火朝天,至今仍可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发现这一点。关于另一种观点,我们可以再一次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他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并不是位最时髦的思想家,他在他的第十五本书《论统一理智斥阿威罗伊学派》(De unitate intellectus contra Averroistas)中指出概念如何在关联无论什么是它们的概念时并没有问题,因为一个概念并不是什么我们对一件事物的理解而就是我们对一件事物的理解。当然,这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见解;但它的错误并不在于概念挡住了通向客体的道路,也不在于概念只是客体的衍生版本。在这一误解的背后隐含着的是概念作为一个人头脑中的图像的不牢靠的隐喻。你也不能通过主张概念是积极主动地建构客体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客体来避开这一圈套。在一大通认识论上的结构主义背后潜伏着视概念为一件准事物的具体化观点,而不是一套行事的方法;因而,比如说,路易斯·阿尔都塞的门徒们(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暧昧地算作他们之中的一员)郑重其事地将世界上的真实客体与一个人对其概念性的建构形成对比,而后者成为了我们唯一能够知道那一客体的事物。这涵盖了“概念”一词的语法错误,而文化理论至今都在全力地掩盖这一错误。 这种反现实主义虚张声势的标榜,倒是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很是相符,完全是反直观的。难道费什真的以为无韵体诗、英雄双韵体诗或是米兰达(Miranda)[46]的性格特征都不是内在于文本而是由读者所授予的性质吗?有人也许会以尼采式的风格为此辩护说内在本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那不过是一种类似日神阿波罗一样的令人不快而引人注目的语言建构罢了。但是这一辩护也使得费什的观点变得无足轻重且不言自明了。如果它对于整个现实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它也就取消了任何通往理解事物的途径,并将事物原原本本地留在了那里。有意义而无力量。断言文学作品缺乏内在本质只会在有人相信起初是存在内在本质的时候才算是有用的。费什要么就得阐清他认为一开始就不存在内在本质,要么就得解释为什么如此喧哗有其内在本质而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chüner)的戏剧则没有。(后者是一段话语的事实并不是答案,因为费什它当作了某种意义上的喧哗来看。)本来,费什欣赏的就是他所说的情况取缔了所有理解的方法,其实他为此而深感其乐融融。他就是那种古怪的实用主义者,并不希望他的理论能在世界上做出什么实际上的差异。他的理论不过是重新描述我们做的任何事情罢了。关键在于解释世界,而不在于改变世界。 对形式主义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okobson)而言,诗学代表了一套“通往信息的陈述”——意味着一个导向我们去关注语言本身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令人费解的是它如何能够清楚地分辨诗歌或小说的形式,或是分辨历史与哲学。此类作品的语言并不总是纯粹工具主义式的事物,邀请我们径直穿过符号而通达所指,潇洒地将自身具有价值的前者弃之不顾。想想塔西佗(Tacitus)、休谟(Hume)、莱基(Lecky)或者E.P. 汤普森(Thompson)。然而,费什并不强调要我们关注于在“美学”层面上被标记为文学的文本,那些文本在语言策略和构思错综上别具风味。他想让我们注意的却是作品的道德内容,对文本语言的敏感性将会带动我们非同凡响的锐聚焦。在亚瑟·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大名鼎鼎的形式与内容二分法之中,作品的语言不过是探索其内容的工具。它仅仅只是一条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些严峻的道德争端面前的事实的线索。 我们可以跟在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内容的形式之后,将这种俯视自然而然地称之为形式的内容。40正如几乎所有的文学哲学家所做的那样,它没有看到一部作品的道德观若是存有任何凝聚力的话,其在形式中的秘诀同在内容中的秘诀会是同样之多的——一篇文学文本的语言与结构或许是所谓的道德内容的载体与起源。一首新古典主义诗歌在英雄双韵体里开掘秩序、对称和均衡;一部被逼着去沿袭台下现实的自然主义戏剧不可能具有任何观点;一部淆乱其时序或令人头晕目眩地转换视角的小说:以上所举的例子皆是艺术形式以自身为道德或意识形态意义的载体的。即使是一段诗歌的胡言乱语、一句双关语或者一个不知不觉的文字游戏,都可以含有一种暗示的道德观点,为自己的创造力而欣喜,焕然一新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释放无意识的联想等等。太不寻常的是文学的哲学在高度追求伦理内容的同时竟然如此频繁地忽视形式的道德性。 彼得·拉马克(Peter Lamarque)同样分离了形式与内容,在道德与认知中割除了有关语言特性的问题。为什么真理与谬误,他非常讲究修辞地询问道他的读者,“与某些东西写得好还是写得差有任何关系?”41一个人只需解除枯燥无味的“写得好还是写得差”这一句子的负担,而去领会一部作品的伦理内省与诸如隐喻、反讽、组织、音调转换、高度修辞、轻描淡写、夸张等风格特征之间的关联即可。“在文学艺术里”,维克托·厄尔里希(Victor Erlich),“意识形态的战役常在隐喻和转喻,或韵律和自由体对立的地域上打响”。42这也适用于一部作品的结构层面。 亨利·詹姆斯后期蛛网式的文体,在拉马克看来,“如果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它有益于文学的呈现人伦之错综复杂、矛盾冲突、脆弱不堪的目的了”。43这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清教徒式文学观。形式上的技法乃是为了服务于超越自身的道德目的而存在的,正如在美国的儿童电视节目中,幼儿的玩耍只能在有启迪人心的道德寓意严格附着于其尾部之时方可接受。可是在《大使》(The Ambassadors)或《金碗》(The Golden Bowl)中对意义细微至极的迂回曲折之筋疲力尽而振奋人心的追寻过程本身就是一类道德体验,而其毫无节制的普鲁斯特式长句,那驱使自身穿越任意数量的缠结从句与绕过任意数量的句法发夹弯道同时不丧失其语义杀伤力的能力,是一种与道德价值有亲密关联的文体表现。 无论如何,“呈现人伦之错综复杂、矛盾冲突、脆弱不堪”怎么样也不只是一个“文学的”目的,这意味着对那一领域的限制。难道一种文体风格不属于一个文学的目的吗?某些传统上所说的文学指的就是一类形式上与道德上尤为难舍难分的著作——这也并非说许许多多“文学的”影响未从相互对抗中产生。4就算不从存在意义上而言,至少就分析意义上而言,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也没必要将此二者当作“有机论上”的个体。不过回应一部作品的“道德内容”(一个自欺欺人的短语)应当是回应由音调、句法、形象、叙事、视角、技法等因素而组成的内容。一条悄无声息地编码在一部文学作品之中的指令就是“根据如何说来判断说什么”。纯文学主义也好,道德主义也罢,他们都是忽视了方法与道德实质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结局。 拉马克和他的同事斯坦因·豪贡·奥尔森(Stein Haugom Olsen)并不接受费什声称文本缺乏内在性质的唯心主义学说。同他一样,他们视文学为一类请求并回馈某种特 《The Event of Literature》读后感(七):伊格尔顿 |《文学事件》第三章:什么是文学(二) 1 现在我们可以转向文学作品的道德维度了。我用“道德”一词来表示人类的意义、价值和品质,而非道义论的、萎顿衰弱的后康德观念上的责任、法律、职责和义务。1它是十九世纪英国的文学符号,从阿诺德(Arnold)和罗斯金(Ruskin)到佩特(Pater)、王尔德还有——至高无上的——亨利·詹姆斯,他们促进了“道德观”这一术语从准则和规范到一个关于价值和品质的问题的转换。这是一件由一些二十世纪卓越的批评家所完善的事业:巴赫金(Bakhtin)、特里林(Trilling)、利维斯、燕卜荪(Empson)与雷蒙·威廉斯(Ramond Williams)俱在其列。 实际上,文学已然成为了后宗教世界道德观的十足范式。对人类品行微妙之处的细致敏感、对价值的费劲鉴别、对如何富裕而自我反省的生活问题的反映,文学作品是道德实践最重要的范例。文学并非如柏拉图所怀疑的是道德观的威胁,而是道德主义的威胁。哪里有道德主义从人类生存的间歇中抽象出道德判断力,哪里就有文学作品将其归还于它们复杂的生存环境。在最妄自尊大的时候,譬如在利维斯及其信徒的作为之下,文学演变成了一场新福音运动。宗教失败了,而艺术或文化将取而代之。 在此观点看来,道德价值倚重于文学作品的形式的程度跟其倚重于内容的程度一样多。诸多观念皆以为然。对一些浪漫派思想家来说,艺术作品各方元素富有成效地共存并生是可以被当做和平团体的楷模的,由此也便有了政治乌托邦。在其限度之内,艺术作品与压迫或统治无关。更有甚者,诗歌或绘画给予了自身特有的形式来作为关联个体与总体的模范。它由一种一般的定律或筹划所管理,但这种定律对个别性是全然知觉的,并不能从他们之间抽象出来。为了将各个要素组织成一个整体,它把每一个元素都提高到了自我实现的程度;而如此这般,自然也是预示了一个个体与集体和谐一致的乌托邦秩序的先兆。 另外,如果艺术作品是道德典范的话,这不该说是因为它不可思议的自主性——那看起来独立自由而不受外部压迫的样子。2而是因为它对一些外部统治权的服从,它效忠于为了它自己的利益而立的定律。在这层意义上,它是人类自由的劳动模范。这里面有形式的伦理和政治利害攸关,而大多数文学的哲学却对此相当无知无觉。 从雪莱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到亨利·詹姆斯和艾瑞斯·梅铎有一条世系是承传道德观自身的想象问题的,从而也就是一种内在固有的美学功能。我们正是凭借着这种直观的感知力来移情进入他者的内在生活,并消解了自我意识的中心化而无私无我地从别人的观点来把握世界的。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依靠其特有结构来成为一种道德实践的,它以从一个意识中心转换到另一个意识中心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整体。文学故而得以在表现道德情操之前就能被当作一件道德事业来看待。这也就导致了艾·阿·瑞恰兹(I. A. Richards)的评论,带着生动活泼以追忆往昔点滴,诗歌确实“能够拯救我们”。他好像没有认识到如果我们的拯救取决于像诗歌这样稀薄而脆弱的东西,我们的情况该有多惨不忍睹啊。 可是,想象有其限度,这一点很多文学类型似乎并未察觉到。只有极少数观念能够毫不含糊地认可之。对想象吹毛求疵看上去会像是对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肆意嘲笑一样显得很不敬。但想象无论如何都不只是一种创造力而已。构想出一场道德败坏的情节的能力与构想积极向上的能力是一模一样的。连环杀人案同样需要足够的想象力。这种功能总是被视为人类最高尚的能力之一,可它也使人紧张不安地接近于幻想,而那正是最幼稚而倒退的能力之一。想象也不是一种特殊或特许的力量。若它是激发马勒(Mahler)第二交响曲“复活”(Resuarrection)的力量,它就同时也是日常认知的基本要素。正是依借了想象使不在场事物化为在场事物的能力,我们方得以拥有未来观,如果没有想象的话我们简直寸步难行。把啤酒罐举到你的嘴唇旁边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你有个模糊的预感接下来罐中储存的东西会因此而滑入你的咽喉。 只有在笛卡尔主义者的世界观里我会需要通过想象的行为从内在来占据你的身体或思想以便知晓你的感觉如何。通常有一种设想认为身体是一块横蛮无理地挫败我们通达彼此内在生活的物质,故而我们需要一些特殊功能(移情、道德感、想象)来侵入彼此内部的情感结构。我们稍后再来审视这种设想。不管怎样,知道你感觉如何并不肯定就能激发我去大慈大悲地对待你。恰恰相反,我大可以亲切和善地对待你而不用在我头脑里再创造你的内部本质世界。我也可以在和一个新法西斯主义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仍旧感到有责骂他的政治观的需要。道德观不是一个关于感觉的问题,所以也就不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问题。 爱其他人首先不是对他们有一种确然的感觉的方法,而是表现一种确然的朝向他们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博爱的范式是爱陌生人而不是爱朋友。在爱陌生人的尝试之中,我们不太会把爱与某人心窝里的温情效应(warm glow)相混淆。种族大清洗并非如一些人所以为那样的是想象力衰竭的结果。不是说纳粹党人无法想象那些他们所杀戮的人是如何感觉的。而是说他们并不在乎。对想象力正如对洞察力一样存在着太多危险的伪善之言了。波尔布特(Pol Pot)[1]与威廉·布莱克和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同样都是了不起的洞察者。当雪莱在他的《为诗一辩》(Defence of Poetry)中写道“宅心仁厚的伟大向导乃是想象”之时,他颇有价值判断地充实了一种尤其腐朽的道德观并且做了一大堆特别模棱两可的设想。3极少有文件像《为诗一辩》那样把诗歌的价值鼓吹到了如此富丽堂皇的地步,也极少有文件如此荒诞地夸大它的重要性。 在阅读文学作品之时,我们兴许会称一些要求介入他人生活的行动观为移情谬误。凯瑟琳·威尔逊(Catherine Wilson)辩论道文学不是关于知道怎样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知道那样的问题,而是关于知道某人感觉是什么的问题。4可是进入某个他人的内部——成为想象性的他们的一部分——并不是指产生我们对他们的知识除非我们在此过程中保持了我们自己的反省能力。纯粹的移情并不和批评认知所要求的理解力相一致。在一种情况下生存,如门罗·比尔兹利所指出的,不会必然地构成知识。5“成为”李尔(Lear)只有在李尔自己把握了自己的真相之时才会要求你把握李尔的真相,而事实似乎远非如此。我们观看《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不是为了感觉愤世嫉俗。我们观看它是为了领会愤世嫉俗的意义,它是关于理智的事情也是关于情感的事情。我们读一首抒情诗不是为了知道诗人在写诗之时她的感觉如何(也许除了纠结于音调和象征之外她一无所感),而是为了通过诗人虚构的感觉之光来观照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新事物。 为什么文学老是被看作一种情感假体或经验的替代性形式呢?一个理由是与现代文明中经验的极端贫瘠有关。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意识形态主义者认为鼓励工人阶级男男女女通过阅读来延伸他们的同感力以超越他们自身所处的状况乃是明智的,一部分原因是这样也许能够培养忍耐力、理解力因此还有政治稳定性,而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办法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们生活的无精打采。宣称这一点对那些文化代表来说决不算是太过分,阅读是一种革命的替代物。6移情的想象在政治上并不如它所看似的那般清纯。 道德价值和文学意义在事实上的共同点乃是二者既不是像水电大坝那种观念上的客体存在;也不是纯粹的主体存在。对一个道德实在论者而言,道德判断遴选出这个世界的真实特征而非仅仅去表达对它们的态度。称反犹主义为道德沦丧不只是标示我碰巧对此的感觉。不称其为道德沦丧就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相关描述,比如说,在一场大屠杀中发生了什么。道德价值在和意义或说实际的艺术作品相同的观念上是真实的。拉马克和奥尔森在《真理、虚构与文学》(Truth, Fiction and Literature)中谈及文学里的“主观知识”时,将其与“外部”世界的科学知识形成对比。但是文学意义,如同艺术作品或道德价值,可不是对头脑中的主观情态的表达。它们是真实世界里的家具的一部分,而且能够在不涉及任何假定主体的情况下被探讨和议论。文学作品确实经常生产生活经验的外观感受,但组成它们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书写符号。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所发生的事情全然是以写作来发生的。人物、事件和情感都不过是在一张书页上的标记的布局。 我们所检验的道德观的“文学”概念与所谓的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的关联远大于其与康德派道义论的关联。7类似于德行伦理学,在一首诗或一部小说中道德判断的客体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或一套命题,而是一种形式的生活品质。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最卓有成效的道德探究,是追问人类是如何繁荣兴旺并实现完满的,而在什么样的实践条件下又是能够行之有效的。在如此的构架之内个体行动或个体命题的判断再来发挥它们的作用。文学作品代表了一种实践或是行知,并且因此而接近于古代的德行概念。它们是道德知识的形式,不过是在一种实践而非理论的意义上的。它们不会在约翰·赛尔(John Searle)具有启发性的归纳术语中被归纳为它们的“信息”。8就像德行,它们有其自身的目的,只有通过施行它们所表示的意味才能够实现它们的目的。德行在世界上有它自己的功效——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它是一个人茁壮成长的唯一通途——但只能借助忠于自己的内在原则。艺术文学作品中也有着类似的东西。 当涉及到我们所言的文学之时,那么,也就不可能简单地将生活经验转化为定律和规范。相反,在一个知行合一的统一体中,这类作品给予我们一种以其他形式轻易无法获得的道德认知。正如彼得·拉马克夹着几分夸大的言辞所说的那样:“当我们由一位艺术家引导着去以全新的方法观照事物之时,采取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甚至无法明确地表达出这种教益,因为这一独特性拒斥了一切普遍化的尝试”。9此类作品的道德含义难以从其特质和肌理之中抽象出来,而这也正是它们像极了真实生活中的行为举止的一点。尽管如此,一个人还是能够在不单单逐句复述文本的情况下做出一些对一部作品道德观点的说明的。实际上,文学批评始终都在做这件事情,有时是以一种高度细腻而精致的方法去做的,即使做的并不完全清晰,不能够同步于拉马克之言“明确地表达[出]一种教益”。但一边被文学作品妙不可言的独特性震撼地哑口无言,另一边归纳出一组道德标签还是有可能的。 与拉马克形成对照,大卫·诺威兹(David Novitz)主张我们能够也应当从文学作品中归纳出教益。“假使,例如”他写道,“鉴于笛福(Defoe)的《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我推想到孤立不再是徒然而又艰苦的,倒是可以激发人类的足智多谋……我兴许会坦率地发觉我改变了对孤立的态度”10 然而,笛福的小说,不是一本童子军手册,也不是一本教育企业家如何去扩张他们利益的教科书。它的道德意味在诺威兹所未见之处与他已见之处相比是同样多的——在它累积的、不屈不挠的线性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叙事形式里,在它简约的、强劲有力的、非比喻性的散文风格里,在它永不满足的对闭合的抗拒力,在它对客体对象首要性质而非次要性质的关注里,在它对故事和道德评价的交织混杂里,在它张弛有度地游走于纯粹偶然性的叙事和天意安排的叙事之间的张力里,在它初始的性格化程式里,在它全然为了自身而明显积聚的插曲里。与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截然不同,这些问题中的极少数能够吸引住文学哲学家的眼球。 一部作品的道德观点,简而言之,在形式上也许与在内容上同等地成为问题——比如,一种情节之间的平行,乃是一个处理一条故事线或描绘人物双向维度的模式的方法。当理查·盖尔提议“我们或许应该在观看或阅读了《小鹿斑比》(Bambi)之后放弃打猎”的时候,他在关于文学作品的道德力量上犯了和诺威兹同样的错误。11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将更倾向于打起猎来。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很是不同,他对于艺术的道德效力有着更为微妙的看法,他把它们看作是对我们概念性和知觉性的所有性能的增大并且因此而提供了我们先前没能把握的描述的方法。12 另一种观点提出的方法认为文学的道德真理大部分是暗含着的。13大体上,它们不是陈述而是被解释出来的。文学作品更适合作为揭露或启示来搭配海德格尔真理的概念而不太适合搭配心灵鸡汤。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Phronesis)那样,它们具体化了一种不能够在普遍化或命题化形式中被充分表达的道德隐性知识的模式,不过也不是说一点也不能够被表达。此类认知形式不可能在习得的过程之中被轻易地抽象出来。这就是当我们主张一篇文学文本的形式与内容须臾不可分离的时候我们想表达的一种意思。此类隐性知识的一个极端案例是明白怎样去吹出《小夜曲》(Eine Kleine Nachtmusik)的口哨,这和吹的行为本身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且不能够去教给另一个人。这种在文学作品中难舍难分的道德悟性由此更像是个人知识而非关于事实的知识。14 即便如此,艺术作品的独特性也并不如拉马克所言的是“拒斥[了]一切普遍化的尝试”。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所注意到的,我们确然可以用普遍化的说法来谈论艺术作品,正如我们可以完美地在普遍化、命题性的形式中对其他人运用我们的个人知识。另一方面,在艺术品自身之中就存在着一种起作用的普遍性形式。对于古典美学而言,如我们所见,作品并不免除于普遍性。反倒是它从头至尾的法度或构思都不过是它个体部分的联合关节而已,所以也就不能从它们之中疏离或抽象出来。艺术因此也就代表了一种启蒙理性模式的替代品,紧咬着具体性的同时又不必松开整体性的大手。它不是一个关于遣散普遍性或妨碍独特性的问题,而是在两者之间领悟一种求同存异的关系。 杰罗姆·斯托尔尼兹(Jerome Stolnitz)对艺术的认知力量颇有些怀疑的味道。15可是他所持有的是一种荒诞不经而又缺乏批判力的科学观,他好像认为自己的真理几乎不需要辩论的余地,这并不能很好地促进他的观点的阐发。(一个人也许能够以一种总是错误的方式来宣称非常科学的真理。)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艺术真理,他论证道,是并不存在的;相反,文学作品倾向于揭示我们在其他根源处已然获悉了的真理。他正确地看到了文学并没有揭示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真理,而不是像F. R. 利维斯那样坚守着有什么道德价值是特定的“文学的”。他没能领会的是文学文本趋向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呈现它们的道德真理;而这意味着此类洞察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形式上和文字上的具体化是不可分割的。(我说“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文学作品也会时不时地提出更为抽象的道德命题,如在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中尤利西斯关于宇宙秩序的侃侃而谈或普鲁斯特对于嫉妒的见解)斯托尔尼兹恐怕我们在从一部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向某种号称其真理的东西的转换中贬抑了它的博大精深。他的错误是把这一真理当作了某种成问题的超出了博大精深的程度的东西——当作了某种从中抽象而出的意义,而不是当作它所采用的质料。 一个人也许能够稍微有所不同地提出这一观点。如果你想要以写作形式去呈现一种道德含义,你或许会感到有必要去编辑、强调、倾向化和风格化你的质料以便阐明它显著的特征。你或许还会发现你自己在组织叙事,或刻画关键情景的戏剧性精彩片段,或塑造活灵活现地阐发你的论点的主要方面的人物形象。总而言之,你会发现你自己在写作一篇小说。把《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变成一部小说就不太需要很多条件。的确,他的作者就曾做梦都向往过写一部除了玩笑之外别无他物的作品,正如瓦尔特·本雅明也曾梦想过写一部只由引文组成的的作品。充实并具体化你的道德含义会意味着将其转化为虚构。道德内容和文学形式将逐渐会合,直到再也无法把它们拆散。虚构的形式与道德的认知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柏拉图所言非虚。柏拉图大多以戏剧的或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通达真理的过程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真理的一部分,而这也适用解释黑格尔和祁克果那截然不同的论述方法。 然而,还存在着比斯托尔尼兹对文学和道德的关联的怀疑更富有生产性的方法。事实真相是文学艺术往往被提为一种比自由道德观略逊一筹的道德范式。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富于暗示性的作品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例子。16努斯鲍姆重视多元性、差异性、结局的开放性、不可简约的具体性、矛盾冲突与复杂性、绝然苦恼的道德决定的困难性(法国人浮夸地称之为“不可能性”)等等。弥足珍贵的价值数不胜数,但努斯鲍姆似乎大体上未曾觉察到它们是怎样社会化和历史化的特性。相比一个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来说,它们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自由派。无怪乎她常常以那个敏锐而苦恼的自由派老前辈作为她的文学榜样,也就亨利·詹姆斯。 毫无疑问,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将其强有力的血统令人钦佩地施用在了这种道德的进路之中,尽管它在詹姆斯和盖斯凯尔(Gaskell)那里比在金斯利(Kingsley)、迪斯雷利(Disraeli)或康拉德(Conrad)那里奏效地多。但是文学艺术的整体不能够被默许地逼迫为高度特殊的道德意识形态。文学和自由并不是同义词,就算它们在大都会的文人墨客看起来是这样的也不行。难道但丁和斯宾塞(Spenser)声名显赫是因为他们对差异性的专注,他们恰到好处的歧义判断,他们绝然不可救药的冲突的价值观,他们对临时暂定和有待深究的而非使人信服和不可变更的真理的选择?并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难道他们就差劲了?弥尔顿是一个有着富有战斗性的、教义的、政治倾向的诗人,他严格地坚持着光明的魄力与黑暗的权力之间的界分。可是即便没有这些个东西他依然是个伟大的作家。 自由派道德观与说教的道德观针锋相对。实际上,现代批评最大的陈词滥调之一就是告诫和布道对于文学艺术的致命性了。“太公然说教的作品,太明显地试图去传授一个信息,”拉马克写道,“几乎不可能具有什么高度价值。”17“公然”和“太明显”使这个观点合宜地颠扑不破;但要是认为哪怕一丁点儿的说教都是令人倒胃的,那么这个判断对于文坛来说也未免太过于保守了,这就像是提出莎士比亚写过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玩意的判断一样。可情况自然并非如此。“说教”仅仅意味着一种告诫,而并没有理由说所有的告诫都必须是虚张声势或者教条主义的。布莱希特的《教育剧》(Lehrstücke)、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的布道词与威廉·布莱克的《地狱的箴言》(Proverbs of Hell)即是说教作品也是强有力的艺术篇章。《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并没有因为它特定的道德目的而沦为使人难堪的二流小说——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托尔斯泰的《复活》(Resurrection)和奥威尔(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同理亦然——更是因为它实施道德目的的方法。这也可以适用于对《疯狂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萨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或易卜生(Ibsen)的《社会支柱》(Pillars of the Community)的思考。比莉·哈勒黛(Billie Holiday)的歌曲《奇异果》(Strange Fruit)就同时是高超艺术和社会宣传。 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文学作品非得经常娴静地为它们医治道德的药丸加糖,以此来遵照拉马克“太公然”建议的那样。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的诗歌就不是特别娴静地邀请美国拿它的原子弹来操自己,但它在文学修辞上的功夫就很到位。自古以来告诫和布道就是文学的功能,也只有在一个“教条”一词与独裁主义产生不祥共鸣的年代,而不是不偏不倚地指称一种信仰的建构体之时,才会使得人们为了具体的信条而不时地对它艺术的畅所欲言抱有谨严的态度。或者实际而言,对于这样的信条抱有谨严的态度。那是一种自由派和后现代的偏见,认为这样的信念是潜在的教条主义(当然,除了独特性的那种情况之外)。更有甚之,信义越是激情昂扬,就越容易滋生褊狭。这般想象是毫无道理的。从巴门尼德(Parmenides)到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历史是散布在非教条主义的信念坚守者手上的。而自由派也同他们的对手一样激情昂扬地坚守着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这种论证普遍运用的是其他人的信念而非某人自己的信念。一个人并不常常能够发现思想自由的批评家会像是谴责那些歌颂五年计划的人那样去谴责为观点自由而高呼的说教作品。 诚然,系统地去陈述教条并不是大多数文学功能的首选方法。但也并不意味着大多数立场坚定的艺术作品都一定是喧哗的和简约的。狄更斯所有作品中最感人肺腑的篇章之一他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里的一段,在乔(Jo)死后他怒不可遏地责骂了从皇后到他的读者的每一个人,这是一段不折不扣的社会宣传。只要搞得漂亮,宣传就不会是不合时宜的。如弥尔顿对于弑君的辩护、雪莱的《暴政的假面》(The Mask of Anarchy)或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反对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宏伟论战所阐明的那样,文学不会不假思索地向政治的党派性妥协。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大量小说是具有政治的党派性的,但批评家极少非难之因为它们大多数分享的是党派性的偏见。在他们眼里,它表现出来的恰恰是未经掩饰的真相。“教条主义”这个词只适用于其他人的信义。只有左派是“立场坚定的”,自由派或保守派可不是。宣称教条的立场不论在何时何地都是对艺术的毁灭的言论,不过是空洞的自由派虔诚。 在我清楚地说明了的“文学”诸要素中,乍一眼看去道德似乎是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显然它对于文学身份来说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它也能够在历史和哲学论述中被找到,更休提什么宗教小手册、生日贺卡、情书、政府关于堕胎状况的报告等等等等了。不过还是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必要条件的。怎么可能会有不探究人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文学呢?在此语境中“道德”的对立面可能是实用上的、技术上的或信息上的。然而,也有可能是抽象的教条,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勇敢的学术的灵魂断言蒲柏(Pope)的《论人》(Essay on Man)不是文学。18可是《农事诗》怎么就被列为文学了呢,它也不过是一本务农指南(其可信度时不时地有点暧昧不明)而完全没有言说人类的信义、主题、热情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呀。它被算作文学的部分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和语言,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和《埃涅阿斯纪》(Aeneid)是用同一支笔写出来的。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被列为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它有不被授予现代科学专著之名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卢克莱修的随笔是用韵文来写的。但丁《炼狱篇》(Purgatorio)里冗长的连绵语段就是由科学和理论的讲解所组成的。 一本都铎王朝膳食手册或十七世纪的关于金鱼配种习性的散文可能不会因为它对人类风俗和道德的特定兴趣的展现而被当作文学,甚至不会因为它被认定为写得格外出色的原因,而是因为它古色古香的语言赋予了它确凿的艺术身份,或许还有它作为一份历史文件的价值的原因。一本在今天写的有关膳食或金鱼的书远不具有被称作文学的资格,除非它是由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在无所事事之时即兴而作的。一部十八世纪论述光学的专著也可能基于同样的理由而被评定为文学。大体而言,一段文字在历史上距离我们的越远,我们越会倾向于把它当作文学。更新近的一些文字则需要更顽强地去为这个值得敬重的身份而奋斗,而且需要更全面地去利用美学特质来如愿以偿。大概我们的银行对账单在几个世纪后会古雅别致地如“骑士传奇”一般被传读下去。 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像鱼类配种这样的散文,尽管是“非道德”、非虚构和(让我们假使)漠不关心地被书写的却仍可以因其“非实用主义”而被视作文学,它们可供反思超出明显功能范围的时机的问题。我们同样应当注意到那些非虚构话语,例如关于皮革产业的政府报告,与虚构的关于公众骚乱的政府报告形成对照而再次为治安部门免责,塑造并挑选了它们的数据,间或地运用了叙事形式,故而也并不是不具有虚构特征的。 克里斯朵夫·纽(Christopher New)问道是否我们“可以因为欣赏(作为文学)一本管道工的指南而赐予此候选人文学的地位”。19倘若它是被华丽动人地写出来的,抑或能够被追溯到1644年,再或者二者皆然,那就很难看出来为什么不行了。它“非道德”的状态大略可以被这些个因素所压倒。E. D. 赫施主张达尔文和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兴许是合格的文学,但一篇关于在旷日持久的知觉孤立后产生的视觉障碍研究的心理学论文则肯定是不合格的。20不过达尔文达到了标准到底是因为他写作地比这个心理学家更娴熟巧妙呢,还是因为历史性的科学作品会被赐予垂涎已久的文学称谓而没那么重要的作品就会被否认呢?要是这篇研究视觉障碍的论文久而久之取得了这种名望呢?在此我们会注意到,偶然地,视文学作品为文字别具特殊价值的观点将把它们的历史性价值同美学价值一样纳入其中。我们大概会仅仅为了它们的历史高度而想要对诸如莱布尼兹(Leibniz)的数学研究这类“非道德”作品使用文学一词。 甚至还可以有毗邻于非道德的虚构形式。一种寡言少语、极端海明威式的叙事(“他离开了酒吧并且绕过睡着了的边境守卫并且风波再起并且感到他的胃再度打绞并且他左眼后部响起轻微的吱吱嘎嘎声就像是眼球在自行脱落一般”)也许会使它的道德意义如此隐晦以至于几乎觉察不了。罗兰·巴特视新小说(nouveau roman)为净化它们道德内涵客体的可贵运动。一部作品的道德观点恰恰在其对质料世界的把捉,还有对起安慰作用的幻觉和朦胧浑浊的情绪的拒斥之中一丝不苟地变得明晰清澈。在文学实在论中,逼真成了它自身的一种道德价值。描述性于此也便成了规范性。 或者来看看这些摘录自阿兰·布朗约翰(Alan Brownjohn)的诗歌《常识》(Common Sense)中的选段吧: 一位务农者,他有 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一星期收入20英镑。 3/4拿来买食物,而家庭成员们 一日三餐。 平均每人每餐多少钱? ——选自皮特曼(Pitman)的《常识算术》 (Common Sense Arithmetic),1917年 一位园丁,周薪24英镑,将被 罚款1/3如果他上班迟到的话。 在26周之后,他收入了 30.5.3英镑。是多少呢 他迟到的频率? ——选自皮特曼的《常识算术》,1917年 ……下方的打印表给出的 是联合王国中靠救济度日者的数目,还有 救济金的总额。 算出每一万人中 靠救济度日者的平均数目。 ——选自皮特曼的《常识算术》,1917年 毋庸置疑这是一首高度道德的诗歌,尽管它并没有对它的记录做出任何道德评价。它对自己的素材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它不过就是用韵文形式来写而已,不过啊不过,这就足以让读者去预设此段篇章她本身的道德态度的暗示了,兴许还可以牵连到福柯式的对统计学本质、社会工程、官方对付穷人的意向等等问题的反映和沉思。 这是不同文化培育不同道德价值的一个标准后现代案例。固然《酒神的伴侣》(Bacchae)或《俄瑞斯忒亚》(Oresteia)的道德规范绝不同于席勒(Schiller)的《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或司汤达(Stendal)的《帕尔马修道院》(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穿越世纪的文学作品所揭示的道德价值是如何地达成共识,尽管指出这一点或许是极其不合潮流的表现。很难想象自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迄帕慕克(Pamuk)的文学艺术主旋律奏响的是严刑拷打和种族清洗的高歌,或是认为仁慈、勇气、爱意是冠冕堂皇的假仁假义而不予理会。对正义之渴望,举例来说,可谓是人类种群及其写作的常青主题,且不论从天南到海北从亘古到如今它采取了什么不一样的形式。这一点能够表明在历史长河之中人文持续性可以是激进的,却不可能反动的。它是后现代注意的盲点之一,偏见地以为圆滑和无常之物总能取代坚持和长久之物,却没能领悟纯然的真理。 2 现在我们来谈而今被称作文学的本质特征之一的非实用性观念。人们有时候会在一段没有直接的或明确的社会功能的文字上使用这个术语,以和违章停车罚单或乳脂软糖秘方形成对照。当文学摆脱了它大多数传统社会功能的束缚之时,这一文学意识就像我们本身一样趋向于在这种时段里积极地活跃了起来。对于描述一首圣母玛利亚赞美诗、一首为驱赶恶灵而构思的圣歌、一场为祝福一位贵族诞辰而举办的假面化妆舞会、一首为庆贺部落军功而写的诗或一篇为赞美一位巧妙地掩盖了他微不足道的智力的君主而作的颂词来说,它的解释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当文学被逐出这些正式的功能之外而它的辩护士通过断言文学作品是自珍自贵的来孜孜以求弥补这种地位的丧失之时,抑或,不能行之有效地应用于一种独特的社会目的之时,它们才会被说成是符合多元化之用的。 这一点,粗略地讲,就是约翰·M.艾利斯(John M. Ellis)在他的《文学批评理论》(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中所拥护的文学概念。艾利斯几乎同意每一个人的观点认为文学文本不能被任何内在固有的本质所识别。他的见解是,取而代之的,它们只有从它们的作用上去看才是可识别的(虽然讽刺的是他没能指明,这些作用其自身可能是非实用性的,诸如优化我们的审美观或深化我们对于残暴的理解能力)。当我们把一段语言当作文学的时候,艾利斯论证道,我们不再让自己(而我们对一段实用性的文字则会)关注它是对是错,也不再关注它是否是那种我们会按照它来行事的信息,如此等等。简而言之,我们不再把它当作我们即时社会语境的一部分来对待了。相反,我们以这样的方法来使用它,把它当作“不特定关联其起源的即时语境的文本”。21有人或许会声称我们抓住了真相,我们看到了文学文本在一些更广阔或更深沉的意义上正确和有用的时刻,而不是单凭经验的正确或直接地发挥其功能。为了补充艾利斯的分析,也有人或许会指出,一篇文本在其根源之处就涵盖了一种同步的聚焦与读者注视的扩展。一方面,我们现在将其当作自身具有价值的东西来对待,而不是采取仅仅工具性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将其从一个具体的语境中释放出来以通向多样性的语境。 鉴于这一考虑而把一篇文本归类为文学乃是做出一个不涉及她的起因或她作为信息传播的功能的决定。(我们稍后再来着眼关于导向所谓言语行为理论的争论。)此类作品既不依赖于它们原始语境的意义,又不根据于它们的成就或其他形势中的东西而被评定。它们是,打个譬喻说,自由漂浮的,脱离了它们的开端而漂泊无依,并随之以一张通行证所行不通的方法而独特便携。一张通行证,诚然,是拿来随身携带的;但它履行其特定的、高度限制的一套功能。一张音乐会门票的功能就更加固定了。文学文本发挥的是那些我们所无法预料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预定阅读它们会在这个或那个形势下有什么“作用”。它们天生就是开放式的,可以从一个语境被运输到另一个并且还在此过程中积聚起了全新的含义。22恰如维姆萨特(Wimssat)和比尔兹利在他们谈及所谓的意图谬误的经典论文中所言,一首诗歌“在新生之初就与作者分道扬镳了”。23 主张文学作品总是易变无常算不得什么新奇的见解。它早有其神圣庄严的历史,最起码也可以追溯到古犹太人采用的《米德拉什》(Midrash)[2]或经学阐释。在巴别塔的坍塌之后聚拢起来法利赛人(Pharisees)研究《摩西五经》(the Torah)就很少考虑从文本中萃取出什么内在含义反倒是侧重于赋予它全新的意义,而且有时候不靠谱地简直使人难以释怀。这帮人,新约的作者们又为了自己的政治神学目的而歪曲他们,就是最初的阐释学家了。圣经文本上的意义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米德拉什”这一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去探索或追究,这一点说得已足够明白了。圣经被看作是无可穷尽的,它在每个时期遇见每位注释者都将被研究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念。除非一段经文能被激进地重新解释为符合今天的需求,不然的话它就会被断定为一件死物。它不得不按照当代的情形被不断地诠释以获得新生。天启乃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而非一个一劳永逸的事件。《摩西五经》被视为一篇根本不完整的文本,每一代的解释者都将促使其臻于完美。他们之中没有哪一个人拥有最终发言权,译解圣经的过程包含了一种永无止境的集体辩驳。24有时候特权地位是归属于口授托拉(oral Torah)[3]的,而写作则助长了意义的实体化。 不过呢,不受其原点所约束的一篇文本,看起来是适用于所有的写作的,尽管它在文学的情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一个程度问题。写作,与无记录的谈话不同,是一种当作者不在场之时能够持续发挥功能的意义模式,而且这一可能性是它永久的结构化特征。“一旦任何述说被写了下来,”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里的苏格拉底评论道,“你将发觉它到处都有,它与完全不相称的人过从甚密的频率都不少于与那些理解它的人相处,并且也完全未能明白它应当与谁交谈而与谁则毫无瓜葛。”25写作中有一种让人担忧的或者说讨人喜欢的混杂而漫无目的的东西,那种东西凭借着其特有的禀性疑神疑鬼地在边境来来回回地巡逻着,像个唧唧歪歪的老酒鬼一样随时准备着去通融任何穿行的陌生人,而且能转达神圣的真理(就好像宗教改革的神使会骤然认出)到违禁或叛变的手上。当值写作之际,你并不知道它会走多远。即便如此,仍有越界的使徒过于幼稚地庆祝无政府主义力量的危险。在有人过于轻率地美化反逻各斯中心之前,在控制压迫势力的情形下倡导经典的关键作用是很有价值的。同样正确的是,正如我早就说的,有些文字的流动性要来的比其他文字大得多。 艾利斯是一种提倡非功能性为文学艺术特有性质的本质主义者。其实,我们应该立刻就能看出这一属性对于文字被列为文学来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同样成问题的比比皆是。首先,艾利斯主张将一部作品剥离其原始语境也就使得它不再为判断的对错所动。我们随后再找时机来质疑这一点。对于对错的漠不关心被普遍认为是虚构性的一种定义,但虚构性和非实用性这两者并没有狼狈为奸。大可以有非实用的文本——在一面墙上喷射着猥亵的词语就为了闹着玩——同时却并不是虚构的。卡尔海因茨·施蒂尔勒(Karlheinz Stierle)讨论道流行小说是处在实用性与非实用性之间的,故而在他的看法里此类作品只不过是作为营造幻觉的工具罢了。26 同样,看到虚构对一段文字和一场实情之间关系的放宽也是很重要的,并且这样做还可以便利艾利斯所想的那种操作。如果不是在所有意义上的话,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的虚构性和非实用性两方面就真存在着联系了。虚构缓和了作品对于实际所负有的责任的重担,并使得它们更容易从中拆分开来。理查·奥曼宣称文学作品缺乏所谓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我们之后再来细查这点,包括了它们作为忽视含有誓言与承诺的日常世界的一个概念,而这也就近似于艾利斯对它们作为非实用性的见解。 相同的效果可以在具自我意识的或修饰丰富的语言中达到,这暗示了一篇文本是作为某些不同于实证状况的报告的东西而出现的。由于诗性符号有着自己本身的物质实在而非直截了当地反映这个世界,在其自身与其所指之间确然存在着匹配的松动,这也近似于虚构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匹配的松动。这类语言手段和非实用性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关系,因为它们也一样,吸引我们所关注的不仅仅只是手头的局面。它们在诸多事物之间扮演的角色像是通告我们有比实用性和即时性更为要紧的东西的信号。还有一种类似的距离是我们把文学作品当作根本的而非实证的道德,故而也就不会照着洗衣单的式样去和详细的情况紧密关联。那么,在此,我所明确的四个文学本质特征也就手拉着手走到了同一个尽头。 艾利斯的论点的另一个问题是就算在现代时期还是有人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具有着不可否认的实用功能的。柏克的政治演讲大概能再一次作为例证吧。我们称这些为文学是因为它们比喻的丰饶、修辞的生动、情感的昂扬、精湛技巧的激动人心等等——于是乎这里的某一个文学成分弥补了另一个的不在场,而后美其名曰非功能性。也可以简单地说柏克关于爱尔兰或美国革命的演讲在他自己的时期是实用的而在我们的时期则是文学。不过那又该怎么去说在他的时期很多人把他的演讲当作诗意化的表演来欣赏这件事呢。 不是所有的文学文本都自由地漂浮离开它们的原始语境的。阿德里安·米切尔(Adrian Mitchell)的诗“给我讲讲有关越南的谎言吧”(Tell me lies about Vietnam )是有意要讨论高度特定的情景的,弥尔顿的十四行诗“复仇,上帝啊,你那被杀戮的圣徒”也是同一个道理。这又不是表明像这样的作品一旦超出了它们当下的局面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是说这些局面对它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艾利斯在此逼得太紧了点儿。这同样事关于非功能性的程度,他好像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实用性与非实用性之间的界限是没有不可渗透的道理的。日常交流也不只是实用而已:想想玩笑、问候、诅咒什么的。或者想想所谓的寒暄交流,集中的焦点在于说话方式本身的表现(“又能与您交流真是太棒了!”)。一篇布道词也许会希望能在它的听众那里产生一些实际的效果,不过估计不是即时即地的那种。 还存在有实用性的虚构,譬如电视里播放的举例说明酒驾愚蠢的情节剧,这刚好和像幽默故事那样非实用非虚构的东西一样是通情达理的。一首马拉美(Mallarmé)的诗确然是非实用的,那么大宪章(Magna Carta)呢,荷尔德林关于悲剧的沉思呢,一篇研究果蝇或美国宪法的科学论文呢?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安放实际作用之时是否增长我们对于果蝇的知识比《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4]还要更实用呢?不是所有的写作只要自由漂浮脱离原旨就能够优雅地享有文学头衔。(美国宪法多大程度上算是文学就是一个在所谓的法律原旨坚守者及其对手之间的争辩地你死我活的问题。)不管怎样吧,难道文学完全就是一个关于我们对写作做了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无关乎写作对我们做了什么?就没有什么文本在某一语境下较其他场合来说更促使了它们对起初状况的脱离,也许借助了它们巴洛克式的语言或不言而喻的虚构地位?真的就没有某种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那些运用英雄双韵体的)正好就做到了分离它们的工作? 艾利斯正确地看到了“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这个用途而构思的文本有可能会被纳入[文学范畴之内],相反有意为了这个用途而构思的文本却有可能会被排除在外”。27这种弹性是他的论点的价值之一。但是他不以,打个比方吧,牛顿、密尔(Mill)或弗洛伊德的写作,而是以日常言语来和“文学”作品形成对比进而论述非功能性的问题就纯属扯淡了。很明显的是诸如“多出色的发型啊!”之类的陈述将在“[它们的]语境过去之后烟消云散”,就像艾利斯所指出的,除非它是某个人生平所受到的唯一一次恭维并且是在苟延残喘等待温情效应的时机,甚至是在这个人的弥留之际。无论如何,恰如其分的比较,都不应该发生在一部文学作品和日常语言之间而是该发生在,再打个比方吧,莱蒙托夫(Lermontov)的《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s)和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之间。在何等程度上后者的意义与价值被制约在它的原始语境之内呢?要是,在某种情况下,一部作品的初始语境不为人知呢?而如果为人所知的话,我们有些时候难道不是会求助于非实用性的作品来帮忙解决关于意义的问题吗?是否有可能一部作品的美学效果的一部分处在了它的原始意义和它对我们现在的意义二者的张力之间?艾利斯是如此狂热地推崇他的论点以至于他把它逼迫得太紧了,毫无必要且难以使人接受,最终雄赳赳地拒斥了一部作品其原始状况的任何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一名形式主义者,而是一名“现世主义者”(presentist):在评估过去的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之时,我们当下的情形总将压倒一切。 可是文本独立性没有必要引发这样一个不太让人信服的反历史主义。一部再循环的作品,或者用布莱希特的术语来说“再功能化的”(refunctioned)作品,依然保有它历史时期的一定性的生产展示。而这能发挥多大影响或许就受制于它如何再功能化,还有再功能化的量。米歇尔·福柯和艾利斯一样厌恶对话语的原始化探究,那将把它捆绑在它原来概念的那个时期里;但是他也毫不怀疑此类话语根本就是历史性的,它们在特定的时期浮现又在其他的时期幻灭。另外,一部作品超越其初始情境的能力,和这些情境的本质,也有着亲密的关系。某些文字依旧能使我们产生共鸣就因为它们的初始语境所赋予它们的独特力量。就此而言,最为坚韧地通过了时间考验的作品也许是,极具讽刺意味的,那些最紧密地属于它本身的历史阶段的作品,或在某种特定方式上属于它自己。 我们决定去非功能性地对待的作品,艾利斯评论道,是那些“值得以文学文本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的……因此,当我们分析一篇文学文本之时,我们总是在对付它的结构特征儿那正是它被高度评价为文学的原因所在”。28但是如果批评分析一成不变地专注于使一篇文本受到高度重视的那些特征的话,那么,正如拉马克和奥尔森一样,很难再会看到有什么文学艺术的否定性批评了。“文学”这一绝对的词语就使得它绝缘于任何无礼的言行了。一部作品是值得探究的这成为了前提条件而非有人对它探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它不值得的话也就没有人会庸人自扰地去探究它了。对于我们所考察过的其他评论家而言,其中存在着某种关于艾利斯价值判断的全过程的循环。 艾利斯对文学的解读有个阶段是描述性与规范性齐头并进的,尽管他坚持要区分它们。如果,他有时似乎在暗示,非功能性比功能性要优越,那么价值就已然熔铸在了文学的定义之内,虽然这里解读的乃是它的非功能性而不是形式、道德或语言特性。一个标准尝试着去为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的空隙构架桥梁,抑或实际与价值之间,这是为了吁请功能概念的帮助:一面好钟是那种能履行保持准确时间的功能的钟,因此它的价值可以被实际地建立起来。艾利斯在某种意义上将此策略树立在了它的头脑之中。在被当作一种实际的情况中,我们能够从一篇文本的非功能性状态走向对它的价值判断。 然而可贵性与非实用性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要的关联。非实用性的写作也有琐细平凡的,譬如我在看到了黑泽码头之后一时兴起胡乱写下的自作多情而又令人作呕的诗句。在他书的另一处,艾利斯看起来好像正式地提出了这个客观事实。“正如一部文学作品必须在根本上被视为一篇履行了某一特定职责并且以某一特定方式被对待的文本,”他写道,“同样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也是在根本上履行好了那个职责并且出众地符合了它作为文学的典型用途的作品。”29那么似乎可贵性与非实用性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区分了,因为我们能够谈论一部作品是如何完美地履行它的(非实用性的)功能的。 人们有时候称呼一部作品为文学,他们是指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概括——它所呈现的东西不只是为了它自己的缘故,那也是可以与一些更广阔或更深入的意义形成共振的东西。30而这显然是与一篇文学文本的虚构身份亲密无间的,和它的非实用特性的关系应该也差不多吧。同时在这两点上来看,它自然比一份工程师报告或一组实践指导来得要更为普遍一些。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所不同于历史的地方正在于它的普遍性。塞缪尔·约翰逊在《拉塞拉斯》(Rasselas)中谈到了对一名作者避免个体性并且致力于普遍命题、广大现象、物种整体问题的需要。华兹华斯写于1802年的《抒情歌谣集》的序言里说到“并非个体与局部,而要普遍与实效”的真理,而乔治·卢卡奇则在《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中坚称一个文本的那些特征是“典型的”而不是纯粹偶发的。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把神话符号看作是在图像的具体性与概念的普遍性之间的过渡地带的漂浮,一种支承文学作品所同样不可或缺的歧义。 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期待远甚于对特殊形象或情境的解读,不论它们有多么地引人注目。相反,我们期待它们在某种朦胧不明的意义上做出超乎它们自身的示意。如同罗伯特·斯特克(Robert Stecker)所指出的,“我们在一个文本的特殊性中寻求某些普遍的意义”。31德莫特·希利(Dermot Healy)的小说《山羊之歌》(A Goat’s Song)中的一个特性乃是冥思“一个蹩脚的故事容纳一个远远超过那些词语意义的真理”的方式。彼得·拉马克讨论道一部文学作品非但呈现了一个世界并且还邀请人们对此作出主题性的阐释,藉此来满足它对更宽广的意义的渴求。32假使这两个层面难分难离,那是因为“某些别的东西”并非全然是另一套体系里的意义,而是一种我们被提供去把握意义的有差别性的方法,一种语言学家称之为领会的实质。我们有意要去留心“诗”或“小说”这样的特定词以便去遵照下述作为例证的实际情况——超越它所描述的事件和它所流露的情感,并理解其中道德含义的暗潮,这可不是洗完指南或《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财经版块所能普遍呈示的情况。 没有什么比雅克·德里达下述对文学与生俱来的两重性的阐明更能启发人心的了: 这种语言所具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寓于语言或写作之中,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标记,如标记一般应当是可重复、可迭代的标记的力量。于是乎它开始与自己产生差异直至足以成为典范并因此而囊括了一种特定的普遍性……不过这种对历史的凝聚,对语言的凝聚,对百科全书的凝聚,仍然在此与一个绝对独一无二的的事件不可分割,还有与一个绝对独一无二的标签,因此也与一个日期,与一种语言,与一种自传体书写不可分割。即便在一种最小值的自传体品质之中也能收集起最伟大的历史性的、理论性的、语言性的、哲学性的文化的可能性——而这就正它所吸引我的地方。33 一部双重书写的语言作品,同时依附于它的独一无二和对它的背离。一首抒情诗或一篇现实主义小说有意呈现的是一种不可化简的具体现实;但是因为它所使用的符号恰恰是可迭代的、可在其他语境中被调动施展的符号,故而任何独特的文学陈述也就在其自身中裹挟了丰富的普遍内涵。于是独一无二性也便表现得像是一个小宇宙,在它微小的区域里凝聚了整个可能的世界。越被塑造或建构成显示这一双重性的文本,也就越约定俗成地接近于文学的条件。文学文本借助于对不可化简的具体情境的刻画代表性地开拓了话语的双重本质,与此同时,借助于语言的特有本质,也便汇入了更多的普遍性。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典范的”(exemplary)。这也同样适用于某些我们对虚构的联想的策略。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 Ponty)的现象学美学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一种相似的双重性。这类艺术品有着一个“显形的”(visible)维度,亦即它们感官上的在场;但几乎像是支架一般支撑其存在的却是整个“隐形的”(invisible)关于重大情境与关系的语境,它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被忽略不计可它却是将艺术品带入前景之中的功能所在。类似的想法启发了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的“世界”(world)的见解。艺术品在梅洛-庞蒂那里占据了知觉与内省之间一个媒介空间,就此意义而言它的感官直觉性流露出了一个更基本的观念语境。这一语境或曰深层结构并不能在作品的角色和事件中立即被知觉到;不过由于它是作为它们的“内层”(lining)而与它们相关的,它也就不完全只是抽象的而已。34 在语言的双重本质里含有着一个悖论性。这个事实就是它越特殊地强劲有力,它也就越博得更多普遍的可能性。在一件事物的所有独特性上刻画它就意味着用语言去进行大肆吹捧;可是那样做的话就会将这个事物包裹在内涵的天罗地网里并且任由想象去围绕着它天旋地转四通八达。你堆砌越多的语言,你越渴望去拍板下你所描述的任何东西的实质(quidditas);然而你却越使得它可以被你所勾出的其他丰富的可能性所置换。恰如一尊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雕塑,它越经修剪,它所隐约闪现的东西越是厚重。 我们所观察的两重性并不足以让所有东西都幸运地被叫作文学。我们有时候去读流行文学(一个在我们说及过的许多理论家眼里矛盾语)仅仅是为了一个有趣的哇啦哇啦的奇谈,那可不存在什么超乎它自身的独特含义。很少有读者冲着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去求助于她的道德智慧。就像理查·盖尔所说的,“文学与它被创作的彼时彼地的社会习俗还有它被写作的风格决定了是否[一部作品]像被倡导的那样是有关于这个世界的普遍真理”。35 况且,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我们要去像一个文本想要我们对待它的方式那样去对待它,正如我们对待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一样。就算一段文字没有表现得要我们去这样做,一位读者始终可以去从事于此类普遍化的操作。我们总是能够去斤斤计较地以为一个安全出口的标志令人想起一种不祥的死亡象征。我们可以认为“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童话大概只想让我们阅读它的故事情节而别无他求,但是并没有理由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我们阅读的时候允许一些充满普遍意义的东西在我们的头脑中闪现,譬如横冲直撞而又无法无天的年轻姑娘们对于当地的治安来说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事实上,很难理解任何的叙事,不论它具有多么顽固的特殊性,怎么可能完完全全地避免得了普遍的涵义。当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文学之时,那就更成为了一个关于编辑和对待特殊性部分地乃是为了普遍性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对虚构的展开了。在虚构中,因为特殊性大多是被编造出来的,它也就更不会去拒斥这一目标的实施了。尽管如此,这种双重编码是不会局限习惯上被称作文学的东西的。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相信文学作品可以与日常用语表达区别开来因为“由个体化言语所传递的信息并不会典范化任何较大的说明性信息,而一部文学作品的言语则会”。36但是一个男人对他的同事夸夸其谈他的性战绩可能会激起的不止是对他自己的一种评判而且还有对于吹牛、性别歧视、男性的自大等等问题的某些普遍化的思索。 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所有的经验都是典范性的。没有人能保证他写的一种思想或感觉在大体上是只有他自己能够明了的,即使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作者也不能这么说。没有什么情感是我可以有而别的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最多只能是我有某些情感而他们恰好没有罢了。去写作就已经是去从事于一种可分享的意义建构了。即使是最显而易见的私人经验也含有一个内蕴的普遍性维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学成为可能。 所谓的文学作品,故而也就蕴含了一种双重阅读,当我们响应具体情境之时我们将其书写下来,使用的却恰好是无意识的、有点不太特殊的语境。因为我们明白《艾玛》(Emma)是一篇小说,所以我们不会把女主角行为的含义框定于她本身,而我们大概会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5]这么做的。当这种双重策略上升到了自我知觉的层面之时,它的名字就叫作寓言了。在文学现实主义看来,它含有在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一种不稳当的平衡。因为一个现实主义文本的普遍看法是实体化在它的具体独特性之中的,这些独特性需要被认识地越使人信服越好。实际上,文学是我们所拥有的对现实最“稠密的”(thickest)的叙述。然而这有可能会削弱作品面面观的力量,将读者的的眼球抽离了那具现化的细节。文本应当顺便提及超乎其自身的事物,但决不能被此类提及所说服而去付出它十足的特殊性以作为代价。具体乃是普遍的媒介,不过也常常会以对它的遮蔽而告终。 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给他的朋友威廉·沃伯顿(William Warburton)写信说他不希望他的读者相信他的小说《克拉丽莎》(Clarissa)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解读,但他也不想承认它只是虚构的而已。他这样说的意思可以有许多种阐释的方法。他也许是说他既想要他的故事有着现实的气息,又不想要读者相信它所描绘的事件是确然发生过的,这样它典范的道德状况就能取得折衷了。要是没有“典型”维度在内,这本书将不过是另一篇对现实生活的报道。我们也将把握不到这部小说作为一个传说的特有本质,它所表现女人不仅仅局限于克拉丽莎,男人也不局限于拉夫雷斯(Lovelace),时空更不局限于十八世纪的伦敦。可是若宣布这本书只是一个虚构的话就会冒着削弱它现实主义影响力的风险,由此也就间接地再一次妨害了它典范的地位。理查生给沃伯顿所讲的意见说明了他想将他的故事悬隔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某一点上,以此来保全他自己在两个世界上的尽善尽美。 在其他事物中对待某些像虚构这样的东西就是让你自身在它周围思考与感受,随心所欲地发挥想象力,以实质之名去拒斥事实的残酷致命性。由于文学作品在对实际有所松脱的层面上是虚构的,它们也就有情投意合的时机来搞这种投机活动。它们可以用骑士精神来对付现实中的冷酷无情,对大呼小叫的现实原则编纂起想象性的臆测而非奴颜媚骨地亦步亦趋。这正是为什么想象会与激进的政治如此频繁地被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若果真这样的随心所欲是将作品保持在一臂之遥的话,它同样也可以意味着一种深切体验。事实上柯勒律治(Coleridge)认为我们越是全神贯注于一部文学作品,我们所给予它的信任也就越少,因为在他的见解中此类信任含有一种意志行为,而太全心全意地沉浸于文本之中会使意志行为变得不太可能。文学作品有能力在它们有形的在场中呈现事物,并藉此以吸引读者进入其中;但是正如胡塞尔现象学所做的它们同样可以把它们空出以便从多样差异的角度去被观照,并将可感知性与临时性结合起来。在距离与引入的相互作用下,它们以非同寻常的集中形式再生产出两重性的或讽刺性的知觉,而这正是归属世界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方法。 3 文学作品是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的文字,这种设想在理论家之间广为盛行。斯坦因·豪贡·奥尔森写道“一部文学作品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欣赏”,搞得好像你可以鉴赏你所不理解的东西一样。37对他而言,如我们所见,阐释一个文本的行为就是认为对它积极的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有人会吃饱了撑地去阐释一部非经典的作 |
精彩图文
 沈潼顾瑾川高赞小说(晴空不许风相别)完结阅读_晴空不许风相别免费看全文
沈潼顾瑾川高赞小说(晴空不许风相别)完结阅读_晴空不许风相别免费看全文 秦锦月季清时(季清时秦锦月)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清时秦锦月小说在线阅读无删减
秦锦月季清时(季清时秦锦月)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季清时秦锦月小说在线阅读无删减 季清时秦锦月(秦锦月季清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无删减_小说(季清时秦锦月)秦锦月季清时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
季清时秦锦月(秦锦月季清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无删减_小说(季清时秦锦月)秦锦月季清时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 《温棠江祈安完整小说》温棠江祈安完结版全章节阅读
《温棠江祈安完整小说》温棠江祈安完结版全章节阅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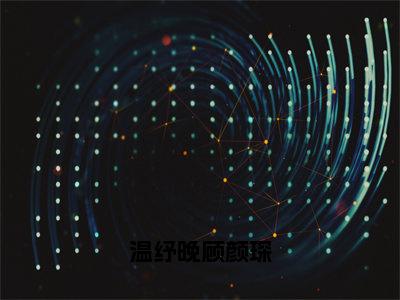 温纾晚顾颜琛:顾颜琛温纾晚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纾晚顾颜琛:顾颜琛温纾晚免费阅读
温纾晚顾颜琛:顾颜琛温纾晚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温纾晚顾颜琛:顾颜琛温纾晚免费阅读 六零军婚,我靠玄学混得风生水起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苏筱柒在线阅读)六零军婚,我靠玄学混得风生水起最新章节完整版阅读
六零军婚,我靠玄学混得风生水起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苏筱柒在线阅读)六零军婚,我靠玄学混得风生水起最新章节完整版阅读 孟栎萤贺廷檐(贺廷檐孟栎萤)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贺廷檐孟栎萤)孟栎萤贺廷檐最新章节列表
孟栎萤贺廷檐(贺廷檐孟栎萤)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贺廷檐孟栎萤)孟栎萤贺廷檐最新章节列表 孟栎萤贺廷檐(贺廷檐孟栎萤)全文免费阅读_贺廷檐孟栎萤(孟栎萤贺廷檐)全文阅读
孟栎萤贺廷檐(贺廷檐孟栎萤)全文免费阅读_贺廷檐孟栎萤(孟栎萤贺廷檐)全文阅读
